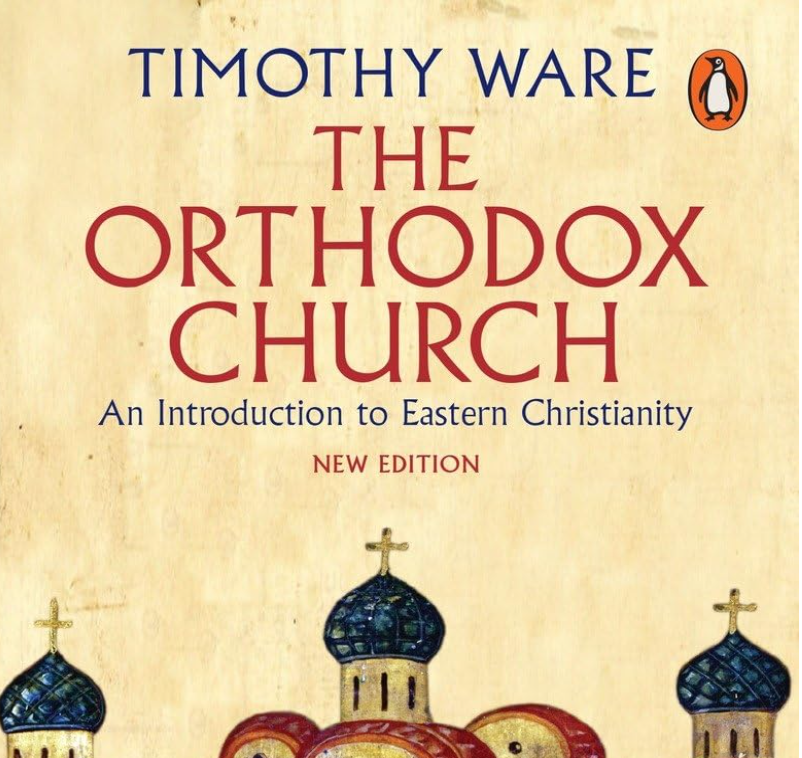-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课系列第三至第五课,第二章,前七次大公会议时期。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三至五课》,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7月5日至8月2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 本讲稿由阿甲修订,很多内容参考这个中译本。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论》,中译田原(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若无特别说明,文字均是维尔主教的中译。若有阿甲的按语,则会写上:“阿甲按”三个字,并以引用符号标出。此篇以体现维尔主教著作为主,若要听阿甲的评论,请听讲座。读者须知,本章三次课,我将按语放置如前,其他如景教不是异端,以及建议不要找神师,而是找神父的,请看笔者写的文章,这里不再复述。
正文
阿甲按:论君士坦丁大帝与米兰赦令
米兰赦令对欧美乃至俄罗斯的宗教态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里我将提供一些评论或点评,说明米兰赦令如何极大地改变了政教关系。首先,它第一个影响是在其他地区和国家,你找不到“僧籍”,所谓僧籍就是僧侣的登记制度,类似户口登记。该制度是在隋朝时期出现的,由于僧侣可免税,结果很多百姓滥用,成为和尚。政府为了管理这些随便变成和尚的人,就出了这个制度。这好像只有在中国出现的制度,在别的国家「我所学有限」,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执政者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意思是说,只要王的政治势力范围内,他理论上就是“上帝”,他想怎么管就怎么管,包括宗教。而隋唐时期,对宗教的管理越发严格起来,你如果想出家,你自己也不能私自出家。只有经过官方的认可,才能算是真正的和尚。在古代,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公度”和“私度”。其中,“公度”是指国家政府认可的度牒。而“私渡”则是指佛教寺院内部私下给予和尚的身份。这种现象在欧美其他国家是否存在呢?至少从印度来看是没有的。不管佛教如何规定,印度政府都不管的。波斯目前根据我的研究也没有这种情况。那么罗马帝国管不管呢?根据米兰赦令,它是不管的,因为是否成为神父,成为修士,那是你的宗教自由,它不管的,因为米兰赦令给了人们宗教自由。所谓自由就是政府不管你。你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想怎么建立自己的教会就怎么建立;你想在哪儿建就去哪儿建。这叫自由的崇拜。而中国政府两千多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米兰赦令这种东西,估计将来也不会出现。因此,早在1600多年前,中国人和欧美人对宗教的态度已经截然不同,基督教在米兰赦令的影响下几乎享受着最大的自由度,其他地区的基督教则殉道的教会自居。甚至现在的一些政治现象,比如自由言论和宗教崇拜的自由。这些其实都起源于君士坦丁。君士坦丁也终结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帝王崇拜。我们知道,在君士坦丁之前,罗马皇帝被视为神灵。所以,现代社会宗教自由的概念从何而来,我可以肯定的说,来自于君士坦丁发布的米兰敕令。所以这是君士坦丁的第一个巨大贡献,
阿甲按:论正统与政治赞助的微妙关系
所谓正统跟政治赞助是难舍难分的。这一点在历史上毋庸置疑。我们说“正统”,其实多多少少与政治支持有关。历史上形成的自称为正统教会的全部源于罗马帝国。我们称之为天主教,他们自称是正统;我们称东正教,他们也自称是正统。我们说俄罗斯教会是正统的教会。为什么说是正统?因为有政治上的赞助。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你说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这只能由上帝来决定。因此,我们要意识到这点,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罗马帝国之外的教会后来普遍被称为异端。因为它们没有获得政治的支持,或者国家的体量比较小,影响力不够大「比如亚美尼亚教会」。比较有名的例子是东叙利亚教会,它从未公开获得政治的赞助,因此它似乎处于一种被政治边缘化或者遭到迫害的状态。一个教派如果受到政治的支持,人们就可能认为它是正统的。然而,一旦不再得到支持,它就会被视为异端。这对吗?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教会的正统性不是源自于政治的赞助和支持「虽然它的影响力很大」而是源自于使徒统绪和大公信仰。正统性应源自使徒的教导。
阿甲按:尼西亚信经可以辨别真伪
第一次大公会议所制定的贡献是尼西亚信经。所有声称自己为基督教派别的教会都承认这一信经,没有一个教派会不承认它。现在如果你能找到这样一个教派不承认尼西亚信经,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它就是异端。如果你发现某个教会声称圣经中有一段话与尼西亚信经不符,因此你相信这段话,这表明该教会可能存在异端倾向。
阿甲按:什么是传统教会的救恩观?
圣阿塔纳修同样总结了关于道成肉身全部目的所在。他说,上帝成为人是为了让我们也能成为神。那么你们会问:早期教会的救恩观是什么?我认为阿塔拿修的这句话基本上概括了早期教会关于救恩的观点。在早期教会中,我们不能说没有因信称义的教导,但在那个时期,这种教导是次要的,或者说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导。教父们的教导不是经常提及,因为因信称义说的怎么信上帝的问题,而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信仰的对象到底是怎样的更为重要。换句话说,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们认为信的是什么远比怎么信才对要重要。阿塔纳修用这句话总结出早期教会的救恩观:上帝成为人是为了让人成为神。我相信所有传统教会救恩观都是这样的,是通用的。或者说我们说的严肃一点,早期教会的救恩观在传统教会是主流的。而宗教改革以后,关于救恩的观点其实发生了变化。我们往往把因信称义与救恩直接等同起来。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教会与早期教会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或者说是我们与传统教会之间的差异所在。
阿甲按:如何避免洗脑?论多元动态的历史观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当然希望历史是黑白分明的。然而,历史是动态的。或者说,现在的学者们试图告诉你一种主题或主旋律的历史观,让你认同。他们通常用简短的口号或一两句话来概括历史。每一个时代的政治执政者,他们都有所谓的主旋律,都有所谓的政治情怀,理想也好,用来重塑历史、重新解释历史。但历史始终不是静态的,始终不是大统一的。它并非始终围绕某个主旋律展开,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群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中,它的表现形式都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历史。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教会历史上都是如此。每个教派都有可能根据自己的要求重新审视历史。它试图给你一个主旋律的概念。它试图说服你加入这个团体。这并不是一种学术精神,而是一种话术。既然你们不懂学术,也就没有思考能力。缺乏思考能力。太好了!我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按照我的主旋律来叙事,宣扬就好了。这样民众一洗脑就信了,信了就可以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尤其是在政治方面,这样的事也太多了。打一场仗,一定要坚持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并指出对方被魔鬼欺骗,务必彻底清除对方。类似的历史事件屡见不鲜,现在依然存在,未来也不会消失。原因很简单:因为人心不干净。所以任何时代都会出现同样的事情。对于我们学者来说,很简单。多学点历史,掌握一手、二手材料,以免被洗脑。
阿甲按:为什么教会会关注社会慈惠事工?
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孤寡老人和孤儿。这些人都需要得到关怀。这种传统的观念并非源自欧美国家。现在的政治体制只是继承了早期的一些理念,并非完全创新的产物。以基督教为国教的执政者们之所以关心社会中的孤儿和寡妇、弱势群体,并关注社会正义,不是来自于执政者本身,而是来自教会。在社会神学和政治神学方面,首先站出来的是金口约翰和大圣巴西尔。他们是这一领域的先驱,Daniel博士的讲座《巴西尔的福利院》就提到这点。他建立了孤儿院、医院和宾馆,为流浪汉提供住宿,抚养灾难中的孤儿。然后他派遣修士们去做这样的社会福利工作。所以这些都是好的。例如,特蕾莎修女所做的这些事情,常人是无法做到的。如果我们有老婆和孩子,怎么会像特蕾莎修女一样,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照顾当地的孤儿,给他们医疗设备,给他们吃的东西,帮助很多被遗弃的脑瘫患儿和即将去世的人,做临终关怀。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他没有时间去做,也没有钱来做。那么当时谁来做呢?教父们来做。因为教父们是关注社会慈惠事工的,是谴责社会不公的,是能从主耶稣基督的角度去看待社会事件的。比如金口约翰经常严厉谴责那个富人奢侈的生活方式,追求名牌和名包,名表、马车,要多奢侈就多奢侈。戴一个耳环,够一个人三年的用度。现在这些现象比比皆是。我们不能消灭贫穷,正如人无法消除自身的贪欲一样,唯一能做的是缓解这种现象。怎么做呢?我想圣巴西尔的福利院和金口约翰的讲道是一个可以好好学习的榜样。
阿甲按:聂斯托留是异端吗?
关于聂斯托留的观点,一些现代学者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整个与基里尔的斗争中,或者说在基里尔打击聂斯托留的过程中,聂斯托留是完败的。他基本上没有机会真正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些现代学者认为,聂斯托留并不一定持有这里所描述的观点。我们现代所知的聂斯托留都是在希腊文献中看到的样子,一些现代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这种看法就是聂斯托留认为基督有两个人格。在教会历史上,一个人一旦被定为异端,他的著作肯定是会被销毁,不能流传的。如今希腊文的奥利金著作是极少的,因为在第五次大公会议也被定为异端,故存留下来的反而是拉丁的译本居多。聂斯托留也是如此,其希腊文著作几乎没有存留,只是大公会议时少数的引用。现代著名叙利亚学者Sebastian Brock撰写的一篇文章,指出亚述东方教会跟聂斯托留几乎没有关系,同时指出叙利亚的人格一词更像上帝的属性,而不是希腊文所认为的实体人格。有些学者根据其叙利亚的译本,认为聂斯托留很可能没有第四次大公会议所谴责的观点。
阿甲按:教会第一次大分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教会的分裂始终是个悲剧。教会第一次分裂发生在5世纪,导致了现今东方教会的各种形态「东正教迦克墩派,非迦克墩派和东叙利亚教会」。这种分裂现象跟一位圣人基里尔分不开关系,他的神学思想是正统的,但在实践层面,他的一些做法却间接导致了东方教会四分五裂的局面。自第四次大公会议之后,亚历山大传统在东正教占据主流「尽管在7-8世纪时被认信者马克西姆进一步修正」。维尔主教说这是一个悲剧,我非常认同,教会分裂不是好事,不应该拿来大肆庆祝。现在的一些学者认为,第四次大公会议是一次失败的会议。虽然它成功地描述了正统信仰,并试图保持平衡,但对双方都不满意「亚历山大派和安提阿派」,结果是两边都没讨好。我完全认识到第四次大公会议的教导和正统性,但是在实际的结果和操作上,它并没有给教会带来合一。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必须承认。现代人反过头来看的话,如果当时他们能够处理得更温和一些,可能就不会发生。
阿甲按:为何叙利亚教会用基督之母的称呼?
上帝之母这一称呼在经历了第四次公会议之后,在东正教中普遍接受。但在叙利亚地区,尤其是东叙利亚教会,据我了解,他们仍然使用基督之母的称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信仰上与东正教截然不同,更不意味着就可以谴责咒诅他们是异端,这是两码事。他们使用基督之母的称呼,有自己的理由和传统。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几乎没有参与到第四次大公会议的争论中。首先,叙利亚教会跟聂斯托留完全没什么关系,一些叙利亚主教认为聂斯托留是个希腊主教,并未在叙利亚教会担任过任何神职,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来自于另一个人,者Theodosius(美索不达米亚的Theodosius)。这个学术传统很早就传给了东西教会。但是,聂斯托留却没有对叙利亚教会产生影响。当然,他们同情聂斯托留,认为他是安提阿对基督论传统的殉道者,或者说整个安提阿的神学传统自古至今都对聂斯托留抱有同情态度。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用基督之母就断定,甚至审判他们是异端。我个人不建议这样做,这是不合理,又没有爱心的表现。
阿甲按:为何新教对大公会议比较无感?
七次大公会议都在拜占庭举行,西方几乎没有直接参与其中的争论,就像公元400年到公元430年的时候,奥古斯丁和佩拉丘的论战,东方也几乎没有参与。对现今中国教会来说,奥古斯丁和佩拉丘的论战确实对中国教会,包括整个新教传统都有着深远影响。因此,中国教会很少提及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怎么联合的,一提到三位一体,只说是个奥秘,然后就结束了。
阿甲按:一代一代按手就算使徒统绪?
使徒统绪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人其实是来自使徒教父爱任纽。他提出了大公信仰和使徒统绪的概念。因为当时有人用福音书伪造了一些文献,如诺斯替主义的文本,导致混淆视听。他强调了使徒传承。他强调使徒统绪,即现今的主教通过按手可以上述追溯到12使徒。目的是要让信徒听这些有使徒统绪的主教们的话,不要听信异端教导。
阿甲按:为何西方较少参与到大公会议的争论中?
其实七次大公会议是以希腊语为主的教义性的争辩,主要发生在东方。希腊语在语法上是一种比较细腻的语言。如果你学过拉丁语,并且又同时学习了希腊语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一点。希腊语比拉丁语更有层次,更加灵活,或者说它更为灵动。因此,它可以在一些概念上产生更加细微的变化;在语法上也可以更细致地发展。不仅如此,希腊人喜欢哲学思辨的风格,其实也传入到教会里面。是怎么传入的呢?是通过七次大公会议,通过教父们对希腊哲学改造传入的,也是希腊哲学接受洗礼,正式进入神学的时期。因为所有的希腊人都精通希腊哲学。就像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秦汉时期熟读秦汉文献,比如《论语》、《孟子》和《庄子》。他们正在通过这七次大会议,将希腊哲学中的这些词汇和对人类思想的那种深邃与好奇心给确定下来。因此,他有很多细微的争辩。我们现代人回过去看看是吧?何必呢?完全听不懂。我们有一次在学校里面讲课的时候,老师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非洲的的东正教徒。他们看到同一本质这个词,感到困惑,就问是什么意思?因为本质一次在圣经中从未出现过,是一个希腊哲学词汇。学校老师就给他们解释,就是信经前面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出自真上帝的真上帝,出自真光的真光。他就是上帝。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也信啊。七次大公会议的争论几乎都与某几个希腊词汇有关。例如,在“和子句”的翻译中,我们很难说其中没有希腊哲学术语和拉丁术语的区别。因为在他们翻译圣经的时候,那个主差遣圣灵和从父发出的圣灵是同一个拉丁词汇。但在希腊文里却是两个不一样的词。因此,希腊文用了另外一个词来表达。再比如,hypastasis在希腊语中最初并不涉及人格,后来才与人格等同,而在拉丁语直接译为人格的。但人格一词,在叙利亚语中却又不同的含义,它没有实体性,而指向属性。拉丁语的一个好处是它的语法结构非常有规律,非常清晰。因此,拉丁人在撰写神学时,并不像希腊人那样自由发挥。我认为,拉丁人的思维方式可能也有所不同。希腊哲学在七次大公会议时期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调整和整顿,从此以后,希腊没有哲学,只有神学。我们称之为拜占庭神学。这段时期的拜占庭神学家们,比如阿塔纳修,巴西尔,神学家格列高利,认信者马克西姆等彻底改造了希腊哲学体系。
阿甲按:为何罗马教皇不是老板?
东正教认为对于教皇也一样。他是罗马教会的首席主教,但并非拥有超越所有主教的职权。因为所有的主教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教皇只是在平等中的首位,并非阶层上的首位。这就像将军司令一样。他的首位是爱中的首位,是家长的长子,而不是老板,军队或官员意义上的首位。
阿甲按:Eastern Church和the Church of the East的区别?
Eastern Churches是罗马帝国所处的西方,对所有在它东部地区教会的通称,有时也叫做Oriental churches。因为这些教会不属于西方,所以他们是东方教会。而The church of the East则是东叙利亚教会对自己的称呼,意思是说,我才是真正处于最东方的哪个教派,其他的教会都不是,所以他们这么自称。The church of the East是亚述东方教派的正式名称,它与东方教会不同,后者是罗马帝国所处的西方对所有在它东部地区教会的通称。
阿甲按:为何历史总是有不可知的部分?论历史的碎片性
我以前把自己定性为一个学神学的人。因为我之前读过几个神学硕士学位。但到博士阶段,你开始学习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历史就像摔碎的玻璃一样。它是一个破碎的过程,历史留下的永远只能是碎片。那么你去尝试,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去尝试理解这个历史当中发生的现象。你能拿到的资源就是这些玻璃碎片。然后你要把它拼凑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还原历史的过程要比侦探还难,因为侦探处理的近期的事件,而历史学家要处理的事物要更为遥远。正因为这种碎片性,我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经得起真正推敲的。学者们的言论也不例外。也许历史留给我们的答案远远比问题少。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读博期间,我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吐鲁番地区的出土文献。这些文献全部都是碎片状,要想了解一些特别细的细节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没有这些材料,你没有办法说什么。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学者,比如一个叫张广达的学者。我觉得还挺佩服他的。他就很坦诚地说:也许这个吐鲁番出土的一些墓葬文书带给我们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解答的多得多。我现在看也是同样的观点。材料不够,不足以证明某些事情,那么宁可不说,存而不论。
阿甲按:亚述东方教会也有圣像?
你们看最近发现的,在新疆的唐朝墩,发现了一个景教寺院。这个寺院有一个讲台,英文叫做“bema”。最近有一些关于这些考古资料的介绍,主要讲述了这个“bema”周围的状况。你可以看到一些类似圣像的这种画作。当然,这个已经具备了唐代那种风格。但是可见这种圣像的流行,并不仅限于东正教,其实同时代的天主教中也有。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传统教会早期都使用这些圣像。
第二章 拜占庭之一:七次会议的教会
所有人都承认七次神圣的大公会议,这是神圣之道,信仰的七根支柱,祂在其上建起他的神圣大厦,大公和普世教会。——俄罗斯都主教约安二世(1080-1089)
(一) 帝国教会的建立
君士坦丁大帝站在教会历史的分水岭上。随着他的皈依,殉道者和迫害的年代结束了,地下墓穴教会开始成为帝国教会。君士坦丁大帝所看见的异象带来的第一个重大结果就是所谓的「米兰赦令」,由他和他的同伴李锡尼(Licinius)皇帝在313年发布,宣告基督教信仰得到了官方的宽容。虽然君士坦丁大帝最初给予的只是宽容,不久之后他说明他意图使基督教超越于罗马帝国其他所有合法宗教之上。在君士坦丁大帝去世的五十年内,狄奥多西(Theodosius)将这条政策贯彻到底:通过立法,他不仅使基督教受到最高的推崇,还使基督教成为帝国内唯一被承认的宗教。这个宗教现在成为了国教。罗马当权者曾经对基督徒们说"不允许你们的存在!"。现在轮到异教遭受压制了。
君士坦丁大帝的十字架异象在他的一生中继续导致两个结果,它们对于基督教帝国后来的发展同样极为重要。首先,他在324年决定将罗马帝国的首都从意大利向东迁至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岸。他在希腊城市拜占庭的地址上建立起一座新都,用他自己的名字将之命名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upolis)。
他这一举措的部分动机是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但也有宗教上的:古老的罗马同异教有关联,受到了太深的玷污了,以致于不能成为他心目中的基督教帝国的中心。
新罗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330年庄重的城市落成典礼之后,他规定不得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异教礼仪。君士坦丁大帝的新都在正教发展历史上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力。
其次,君士坦丁大帝于325年在尼西亚(Nicaea)召集了第一次基督教会全体的大公会议。如果罗马帝国要成为一个基督教帝国,那么君士坦丁大帝希望看到它建立在正教信仰的坚实基础上。尼西亚大公会议的责任是详细规定信仰的内容。没有什么比尼西亚大公会议这个外部环境更能清晰地体现出教会和国家的新关系。
皇帝本人主持会议,如同参会者之一凯撒利亚(Caesarea)主教优西比乌(Eusebius)说的那样,“像上帝的天国使者”。在会议结束时,所有主教同皇帝一起进餐。优西比乌写道:“宴会的排场辉煌至极,难以形容。带着出鞘利剑的禁卫部队和其他军队围绕在宫殿入口,敬拜上帝的人们穿过这些人,毫不恐惧地走入帝国殿堂的最深处。一些人和皇帝一起围在桌旁,其他人靠在另一边的沙发上。人们会认为这是一幅基督王国的景象,是一个梦想而非现实。“1
*1 《君士坦丁传 》3章
自从尼禄把基督徒当作活火把,在晚上照亮其花园的时代以来,情况无疑发生了变化。尼西亚大公会议是七次全体会议中的第一次;像君士坦丁大帝的城市一样,这次会议在正教历史上占据着中心的地位。
米兰赦令、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尼西亚大公会议这三件事情标志着教会的到来时代。
(二) 前六次大公会议(325-681)
在早期的拜占庭时代,七次全体会议主导了教会的生活。这些会议完成了两个使命。
首先,它们澄清和阐释了教会的有形组织,明确了五个大的主教教区或宗主教区的地位,它们开始为人所知。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大公会议一劳永逸地确定了教会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神圣『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所有基督徒共同认为这些信理是"神秘的”,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力和语言。当主教们在会议上拟定定义时,并不认为他们已经解释了神秘;他们只是寻求排除一些错误的言说方式和思考方式。为了防止人们陷入错误和异端,他们在神秘的周围筑建起围墙;别无其他。
会议讨论有时听上去抽象而遥远,虽然它们由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所引发:人类的救赎。
《新约》教导说,人由于罪而同天主相分离,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自己的罪所树立的分离隔阂。因此上帝采取主动的方式:祂降生成为人,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由此使人摆脱罪和死的束缚。这是基督信仰的中心要旨,会议着手保卫的就是这个救赎思想。异端是危险的,需要受到谴责,因为它们损害了《新约》中启示所蕴含的教义,在人和上帝之间设置了障碍,因此不可能使人得到完全的救赎。
圣保罗宗徒运用「分享」(sharing)这个术语表达了这个救赎思想。基督分担我们的贫困,叫我们分享祂神性的富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你们成了贫困的,叫你们因祂的贫困,可以成为富足的”—《林后8:9》。在圣约安的福音书中,可以找到有轻微差异的同样思想。基督说祂已经赐予祂的门徒分享上帝的荣耀,祂祈祷他们会实现与上帝合一:“您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约17:22-3》。希腊教父在字面意义上使用这些以及与这些相似的文本,敢于谈论人类的『神化』(deification希腊文为theosis)。他们争论说,如果人要分享上帝的荣耀,如果他们要与上帝"完完全全地合一”,这实际上意味着人必须被『神化』:恩宠让他们在本质上成为天主之所是。圣阿塔纳修(St.Athanasius)相应地概括了道成肉身的目的:“上帝成为人,以使我们成为神。“2
*2《论道成肉身》(On the Incarnation)
现在如果"成为神 theosis”,若要可能,救赎者基督必须既是完全的上帝又是完全的人类。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能拯救人;因此基督若要拯救人类,祂必须是上帝。但是只有当祂是像我们一样的真正的人时,我们人才能参与祂为我们所做的活动。道成肉身的基督在天主与人之间架设起桥梁,祂既是上帝又是人。我们的主许诺:“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1:51》。使用梯子的不仅有天使,还有人类。
基督必须完全是上帝又完全是人。所有的异端思想都相应地损害了这个至关重要的主张的某部分。要么’基督低于上帝’(阿里乌主义 Arianism);要么’基督的人性同神性分离,具有两个位格而非一个位格’(聂斯托利主义 Nestorianism);要么’基督不是作为真实的人临在’(基督一性论 Monophysitism),(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ism)。每次会议都捍卫这个主张。前两次大公会议在4世纪召开,集中关注前面的部分(基督必须具有完全的神性),制定出关于圣三一教义。下面的四次会议在5、6、7世纪召开,转向了第二部分(基督具有完全的人性),也致力于解释人性和神性如何在一个单一位格中结合。捍卫圣像的第七次会议看上去有些偏离这些议题,但是像前六次会议一样,它最终关注的还是道成肉身和人类的救赎问题。
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主要工作是谴责阿里乌主义。阿里乌是亚历山大的一位神父,他主张圣子次于圣父,在上帝与创造之间划出分隔线,他认为圣子是受造物 : 虽为真实的高级受造物,但依然是受造物。他的动机无疑是要保护上帝的独一性和超越性,但是却使基督不再是上帝,其思想的结果是使人神化成为不可能。大公会议对此回答说,只有当基督是真正的上帝时,祂才能使我们与上帝合一,因为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向人开启合一的道路。基督与父『同质』(one in essence,homoousios)。祂不是半神半人(demigod),也不是高级受造物,而是圣父是上帝那个意义上的上帝:『出自真神的真神』,会议在其所指定的信经中宣称,『为父所生,并非被造,与父同质』。
尼西亚大公会议也涉及教会的有形组织的问题。它挑选出三个伟大的中心: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提阿(教规6)。它也规定耶路撒冷主教教区虽然服从于凯撒利亚的都主教,但是应该被赋予紧随上面三个主教教区其后的地位和尊严。(教规7)君士坦丁堡自然没被提及,因为直到五年之后,它才正式成为新的首都;同以前一样,它继续服从于赫拉克里亚(Heraclea)的都主教。
在381年于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二次大公会议延续了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工作。这次会议拓展和修改了《尼西亚信经》,特别发展了关于圣灵的教义,大公会议宣布圣灵同圣父和圣子一样是上帝:『它出自于父,与父和子同受敬拜,共享荣耀』。大公会议修改了尼西亚第六教规的条款。君士坦丁堡现在已经成为首都,它的地位不能再受到忽视,它被排在第二位,位于罗马之后,而在位于亚历山大之前。「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应该享有仅次于罗马主教的特殊尊荣,因为君士坦丁堡现在是新罗马」(教规3)。
在大公会议给出的定义背后,隐现着神学家的工作,他们使得会议使用的词语具有了精确性。亚历山大的圣阿塔纳修的最杰出的成就,是为《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的关键词homoousios确定了完整的含义:同质。
为他做补充工作的有三位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n)教父,纳西昂的圣格里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在正教会内被人称为神学家格里高利(?329-?390),圣大巴西略(Basil the Great,?330-379)和他的弟弟尼撒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卒于394年),三位圣徒。
当圣阿塔纳修强调天主的同一性——父子同质(ousia)时,卡帕多西亚教父强调天主有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hypostasis)。他们在天主的’三’与’一’之间保持着精妙的平衡,为经典的圣三一体教义确定了完整的含义,三位一体(three persons in one essence)。教会在一代内拥有四位如此地位的神学家,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381年以后,除了在西欧的某些地区,阿里乌主义销声匿迹了。大公会议所商讨的争议是第三条教规,罗马和亚历山大两方都对这个教规不满。旧罗马想知道新罗马的要求何时休止:不久以后君士坦丁堡不会想要居于首位吗?于是旧罗马选择不理睬这条冒犯性的教规,直到拉特兰(Lateran)宗主教会议(1215年),教宗才正式承认君士坦丁堡争取第二位置的要求。(君士坦丁堡在那时落入十字军之手,其主管者是一位拉丁宗主教。)但是这条教规对于亚历山大来说也同样是一个挑战,它在那时已经居于东方之首位。接下来的七十年见证了君士坦丁堡与亚历山大之间尖锐的冲突,亚历山大在其间一度获得了胜利。亚历山大取得的第一个主要胜利是在橡树会议上(Synod of Oak),亚历山大的西奥菲勒斯(Theophilus)使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圣约安·克里索斯顿(St.JohnChrysostom),『圣金口约安』(?334-407)遭到罢免和流放。约安是一位善于雄辩的传教士——他的讲道一定经常持续一个小时或以上——他用通俗的方式表达了圣阿塔纳修和卡帕多西亚教父提出的神学思想。他过着严厉而简朴的生活,对穷人的深深同情和对社会正义的熊熊热情激励了他。在所有教父中,他或许是最受正教会喜欢的神父,他的著作得到最广泛的传阅。
亚历山大里亚的第二个主要胜利是由西奥菲勒斯的侄子和后继人,亚历山大里亚的圣西里尔(St.Cyril,
卒于444年)取得的,他在于艾弗所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431年)上,使另一位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聂斯托利(Nestorius)下台。但是在艾弗所,还有比两大宗主教教区之间的较量更为重要的其他事情。
自从381年已经休止的教义争端,现在再一次出现,这次集中在基督的位格而非圣三一的问题上。西里尔和聂斯托利同意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是圣三一的其中之一,但是在论述基督的人性,和解释神性和人性在单一位格中结合的方式时,他们之间有分歧。他们代表了不同的神学传统或派别。聂斯托利接受安提阿学派的教育,维护基督人性的完整性,但是在人性和神性之间做出了截然的区分,致使他最后走到了非一个位格,而是两个位格共存于一体的危险境地。西里尔拥护对立的亚历山大传统,其出发点是基督位格的合一性,而不是基督人性和神性的差异,但是他对基督人性的讨论不如安提阿学派生动。如果两条道路走得过远,都可能导致异端,但是教会需要两者的平衡,以形成完整的关于基督的画面。两个学派不是互相平衡,而是走入冲突之中,这是基督教国的悲剧。
聂斯托利拒绝称童真女玛利亚为『上帝之母』(Theotokos),这使得争端加剧。这个称呼已经在大众的宗教敬礼中被接受,但是对于聂斯托利来说,它似乎意味着基督人性和其天主性的混淆。他争辩说,玛利亚只能被叫做「人之母」或者至多被叫做「基督之母」,因为她只是基督的人性之母,而非基督的神性之母,安提阿学派的"分离主义"在他这里一目了然。受到会议支持的西里尔用『道成肉身』(约1:14)的经文做了回应: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因为"她生下了道成肉身的上帝"3。
*3西里尔 《十二咒诅》首篇
玛利亚所生下的不是一个同上帝有着松散联合的人,而是一个独立和不可分的位格,祂同时是上帝和人。上帝之母这个名字保卫了基督位格的合一性:否认她的这个名字就是将道成肉身的基督一分为二,打破了上帝与人之间的桥梁,在基督的位格中间建立起一道分割之墙。因此,我们看到艾弗所大公会议涉及的问题不仅是宗教崇拜的名称问题,还是关于「救赎」这个中心要旨。如同「同质」一词居于圣三一教义之首一样,「上帝之母」一词也在道成肉身的教义中居于首位。
在449年于艾弗所所举行的第二次大公会议上,亚历山大又获胜了,但是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人感到,这次会议将亚历山大学派的立场推至了极端。亚历山大的狄奥斯科鲁(Dioscorus)是西里尔的后继者,他坚持基督只有一性(physis);拯救者出自两性,但是他在道成肉身之后,只有唯一的"道成肉身的神性”。这种立场一般被称为「基督一性论」。西里尔本人确实使用过这样的语言,但是狄奥斯科鲁删掉了西里尔在433年做出的,向安提阿学派让步的平衡性论断。在许多人看来,狄奥斯科鲁否定了基督具有完全的人性,虽然他们对他的立场的解释也不完全公平。
仅仅在两年之后的451年,玛西安(Marcian)皇帝重新将主教们召集到卡尔西顿(Chalcedon),拜占庭教会和西方教会视之为第四次全体会议。钟摆现在摆动到安提约基亚学派的一方。会议拒绝了狄奥斯科鲁的基督一性论立场,宣称基督虽然是一个单一的、不可分离的位格,但是祂不仅出自两性,还具有两性。主教们称赞罗马教宗圣利奥一世(St.Leo the Great,卒于461年)的《大卷》(Tome),它尽管强调了基督单一的位格,同时也清晰地阐述了两性之间的区别。
在信仰的公告中,他们宣布他们相信「同一个圣子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是真正的上帝和真正的人……公认其在两性中不混淆、不变动、不可分、不相离;两性之间的区别决不因联合而消失,相反,每一性的独特属性都被保留,两性在一个位格和一个本质(hypostasis)中结合。」
我们注意到,卡尔西顿定义的目的不仅针对基督一性论(两性不混淆、不变动),还针对聂斯托利的追随者们(同一个圣子……不可分、不相离)。
但是卡尔西顿不仅挫败了亚历山大学派的神学,它也挫败了亚历山大获得东方最高治理权的要求。卡尔西顿会议的第二十八条教规确认了君士坦丁堡的第三条教规,规定新罗马的地位和尊严紧随旧罗马其后。利奥教宗拒绝了这条教规,但是东方自此之后就承认这条教规。大公会议也使耶路撒冷从凯撒利亚教区独立出来,使其在大主教教区中排名第五。后来被正教徒称为的五大宗主教区的制度现在形成了,五个大的主教教区在教会中拥有特殊的荣誉,它们之间具有固定的优先次序:按照地位排序依次是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五个全部声称具有使徒基础。前四个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城市;新增加的第五个是由于其是基督被钉十字架和从死中复活的地方。这些城市的主教都得到了宗主教的头衔。除了被艾弗所会议赋予独立,从此一直保持自治的塞浦路斯之外,整个已知世界的管理范围都在五个宗主教区之间划分。
当谈论正教会的五大宗主教区这个概念时,必须避免两个可能的误解。首先,宗主教和都主教体系是一个教会组织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教会圣职的视角,而从神圣权利视角来看待教会时,那么我们必须说无论主教所掌管的城市是低微的或高级的,所有主教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所有主教都平等地分享宗徒统绪;所有主教都拥有同样的圣事权力,所有主教都是被上主所任命的信仰导师。如果出现教义争端,由宗主教来表达其观点是不够的:每一位教区主教都有权利出席全体会议,有权利讲话,有权利投票。五大宗主教区的制度没有损害全体主教本质上的平等,它也没有剥夺圣伊格纳修赋予各个地方团体的重要性。
其次,正教相信教宗在五个宗主教中具有特殊地位。正教会不接受1870年梵蒂冈决议提出的,罗马天主教今天倡导的教宗权威的信理;但正教同时不否认神圣和宗徒的罗马主教教区具有首席荣誉,拥有倾听全部基督教世界呼声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注意我们使用的词语是『首席』(primacy)而非「最高」(supremacy)。正教会认为教宗是"在爱中掌管"的主教,这个改编短语出自圣伊格纳修:正教相信罗马的错误在于将首席或"在爱中掌管"变为最高的外在权力和管理权。
罗马之所以享有首席权,来源于三个因素。第一,罗马是圣彼得和圣保罗殉道的城市,圣彼得还是那里的主教。正教会承认圣彼得是众宗徒之首:它没有忘记福音书中著名的"彼得经文"(太16:18-19;路22:32;约21:15-17),虽然正教神学家对这些经文的理解同现代的罗马天主教注释者颇不相同。当许多正教神学家说不仅罗马主教,而且所有主教都是圣彼得的继承人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承认罗马主教是圣彼得的特殊继承人。第二,罗马主教教区的首席权也归功于罗马城在帝国的地位:她是首都,是古代世界的主要城市,当君士坦丁堡建立之后,她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这样的地位。第三,虽然偶有教宗陷入异端,但是在教会历史上的头八百年中,罗马主教教区在整体上以其信仰的纯洁性而瞩目于世:其他宗主教区在经历重大的教义纷争时摇摆不定,而罗马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立场坚定。当反异端的斗争形势严峻时,人们能够充满信心地求助教宗。上帝所任命的信仰导师不仅有罗马教宗、还有所有的主教;但是因为罗马主教教区在实践中教导信仰,极其忠诚于真理,早期教会的所有人们首先向罗马寻求指导。
但是对于宗主教的原则,也适用于教宗:罗马的首席不能颠覆所有主教在本质上的平等。教宗是教会的第一主教——但是他是平等者中的第一。
艾弗所和卡尔西顿是正教的一块基石,但它们也是一块沉重的冒犯基石。阿里乌主义者逐渐妥协,不再是分裂的教派。但是至今还有一些基督徒属于东方教会(他们常常被错误地称为"聂斯托利主义者"),他们不能接受艾弗所大公会议的决定,认为艾弗所会议把童贞女玛利亚称为『上帝之母』是错误的;至今还有遵从狄奥斯科鲁的基督一性论教义的非卡尔西顿主义者,他们拒绝卡尔西顿会议的定义和圣利奥教宗的《大卷》。
东方教会几乎全部位于拜占庭帝国之外,在拜占庭历史上人们对其知晓甚少。但是非卡尔西顿派的大部分成员,特别是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成员,是皇帝的臣民,使他们同拜占庭教会恢复交流的尝试多次出现但却未有结果。文化和民族的冲突常常使神学差异更为痛苦。
埃及和叙利亚在语言和背景方面的主导因素都是非希腊的,它们愤恨希腊化君士坦丁堡在宗教和政治事务上的力量。政治分离主义因此强化了教会的分裂。若不是因为这些非神学的因素,双方或许已经在卡尔西顿会议之后达成神学共识了。许多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非卡尔西顿派」和「卡尔西顿派」(即正教徒们)之间的分歧基本上是术语分歧,而非神学分歧。双方在不同的意义上理解『本性』(physis)一词,但是他们都着眼于证实同一个基本真理:救赎者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和完全的人,虽然祂是一而不是二。
卡尔西顿的定义,由其后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两次会议做了补充。第五次大公会议(553)根据亚历山大派的立场重新解释了卡尔西顿的决议,寻求使用比卡尔西顿会议更具建设性的术语,解释基督的两个性质如何联合形成一个单一位格。第六次大公会议(680-681年)谴责了基督一志论异端,后者认为虽然基督具有两个性质,但是由于祂只有一个单一位格,所以祂只有一个意志。会议回应说,如果基督具有两个性质,那么祂也必须具有两个意志。会议感觉到基督一志论者损害了基督人性的完整性,因为不具备属人意志的人性是不完整的,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既然基督是真正的上帝,也是真正的人类,祂必须具有属上帝的意志,也必须具有属人的意志。
在第六次会议的前五十年间,拜占庭面对着一项突然而骇人的发展:伊斯兰教的崛起。穆斯林扩张的最突出之处是其速度。当默罕默德在632年去世时,他的权威几乎没有扩展到汉志(Hejaz)之外。但是他的信徒在15年内攻下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在50年内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几乎拿下了该城;在一百年内横扫北非,推进到西班牙,迫使西欧在普瓦捷战役(battle of Poitiers)中拼命战斗。阿拉伯人的入侵被称为"向外扩张,各个方向都有成群前来寻求食物、掠夺和征服的突袭兵。古来的帝国无力抵抗。“4
*4《拜占庭:导论》
基督教国艰难地存活下来。拜占庭失去了东方的属地,亚历山大、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三个宗主教区转归异教徒管理;在东方的基督教帝国,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现在没有竞争对手了。此后的拜占庭在很长的时期不断受到穆斯林的进攻,虽然它支撑了八百多年,但最终却屈服了。
(三)圣像
681年会议的召开并没有终止基督位格问题上的争议,这场争议以不同的形式延续到八世纪和九世纪。争议的中心是圣像,基督,上帝之母和圣人的图画在教会和私人家中被保存和敬拜的问题。
“圣像反对者"或"圣像摧毁者"怀疑一切描绘人类或上帝的宗教艺术,要求摧毁圣像;反对方的"圣像护卫者"或"圣像崇拜者"强烈捍卫圣像在教会生活中的地位。这场斗争不仅仅是基督教艺术的两个观念之间的冲突。它涉及更深刻的问题:基督的人性的特征,基督教对于物质的态度,基督教救赎的真正意义。
圣像反对者可能受到犹太教和穆斯林观念的外部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拜占庭帝国爆发首次反圣像争论的前三年,穆斯林叶吉德(Caliph Yezid)命令移去其领土内的一切圣像。但是反圣像争论不仅仅是从外部传入的;基督教内部始终存在着一种"清教徒的"观点,因为在所有图像中看到了潜在的偶像崇拜而谴责圣像敬礼。当伊苏里亚(Isaurian)王朝的皇帝们破坏圣像时,他们得到教会内部的大力支持。
持续了大约120年的反圣像争论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段时期始于726年利奥三世开始破坏圣像时,在780年艾琳(Irene)皇后暂停迫害时结束。敬礼圣像者的立场受到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公会议(787)的支持,这次会议同第一次会议一样在尼西亚召开。会议宣布教堂必须保存圣像,圣像应该和其他物质象征,如「珍贵和赐予生命的十字架」和福音书,受到同样的尊敬和敬礼。亚美尼亚人利奥五世(Leo V the Armenian)在815年发起了新一轮的破坏圣像运动,这运动一直持续到另一位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在843年再次恢复圣像,这次恢复是永久的。
圣像在843年的最终胜利被认为是『正教的胜利』,在『正教主日』,即在四旬斋期的第一个主日举行的特别崇拜活动,就是纪念这个胜利的。在第一段时期,圣像的主要保卫者是大马士革的圣约安(St.John of Damascus,?675-749),在第二段时期是斯托迪奥的圣西奥多(St.Theadore of Stoudios,759-826)。圣约安因为居住在穆斯林地区,位于拜占庭政府范围之外,能够更加自由地工作。伊斯兰教在其后也不止一次地无意地充当了正教的保护者。
正教的独特特征之一,就在于它赋予圣像以地位。今天的正教圣堂内充满了圣像:分隔圣堂和建筑的是一道坚固的屏风,叫做『圣幛』,上面布满了圣像,其他的圣像被放置在教堂四周的特殊圣壇上,墙壁的壁画或马赛克画上也布满了圣像。正教徒拜倒在这些圣像面前,亲吻它们并在它们面前点燃蜡烛;神父为它们焚香,在游行队伍中带着它们。这些姿势和行动有什么意谓?圣像表示什么?为什么大马士革的圣约安和其他人认为它们重要?
我们将首先思考圣像摧毁者针对敬礼圣像者提出的关于偶像崇拜的指控;然后思考圣像作为教导方式的正面价值;最后思考它们在教义方面的重要性。
(1) 偶像崇拜的问题
当正教徒亲吻圣像或拜倒在圣像面前时,他们并没有犯偶像崇拜之罪。圣像不是偶像而是一种象征;形象敬奉的对象不是石头、木头和涂料,而是被描绘的人。
尼亚波利的利安提(Leontius of Neapolis,约在650年去世)在反圣像争论爆发之前就已经指出:
‘我们不向木头的性质进行敬礼,但是我们尊敬和向之敬礼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祂……当十字架的两个梁柱结合在一起时,我敬拜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像,但是如果梁柱被分开了,我会扔掉,烧了它们。
因为圣像仅仅是象征,正教会不崇拜(worship)它们,而是尊敬(reverence)或敬奉(venerate)它们。大马士革的圣约安仔细区分了对物质象征的相对敬奉和只针对上帝的崇拜。
(2) 圣像是教会教导的一部分
利安提说圣像是"打开的书,为了使我们想起上帝”;教会为了信仰之教导而把它们当成一种手段来使用。缺乏学识或缺乏闲暇去学习神学著作的人只有进入教堂,才能看到基督宗教的所有神秘在他面前的墙壁上展示出来。圣像崇拜者说,如果一位异教徒要求你向他展示你的信仰,就带他进入教堂,把他领到圣像面前。圣像以这种方式成为神圣传统的一部分。
(3) 圣像的教义重要性
我们在这里深入到反圣像争论的真正中心。假如圣像不是偶像,假如它们有助于教导;它们不仅是可被允许的还是必需的吗?拥有圣像是绝对必要的吗?圣像崇拜者认为如此,因为圣像拥护了完整和正确的道成肉身的教义。
圣像反对者和圣像崇拜者一致认为上帝的永恒本质不能够被表现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约1:18》。但是,圣像崇拜者继续说,道成肉身已经使表像的宗教艺术成为可能:上帝能够被描绘,因为祂成为了人,具有肉身。
大马士革的圣约安认为,能够用物质形象描绘具有物质形体的祂:
‘非形体和不受限的旧约的上帝根本不能被描绘。但是上帝现在出现在肉身之中,在人群之中生活,我制作天主的形像让人看。我不崇拜物质,我钦崇物质的创造者,祂为了我而成为物质,屈尊留在物质中,祂通过物质实现对我的救赎。我不会停止崇拜使我得救的物质。’——《论圣像》(On Icons)
圣像反对者拒绝对神的一切描绘,未能够充分认识道成肉身的内涵。他们就像许多清教徒那样,陷入了一种二元论。他们认为物质是污秽的,需要一个不再同物质的东西相接触的宗教;因为他们认为神性之物必定是非物质的,但是这使基督的人性和形体无处安放,违反了道成肉身,忘记了我们的身体同我们的灵魂一样必须被拯救和被改观。反对圣像的争论因此同早期的关于基督位格的争论紧密相联。它不仅是关于一场宗教艺术的争论,还是关于道成肉身,关于人类救赎,关于整个物质宇宙救赎的争辩。
上帝具有了物质形体,也就证明物质能够被救赎,大马士革的圣约安说:“成肉身的道已经神化了肉身”。上帝已经『圣化』了物质,使它"承载灵性”;如果肉身成为圣灵的载体,那么木头和涂料也能成为圣灵的载体,虽然方式不同。同正教的圣像教义紧密相联的是正教相信上帝的整个受造物,包括物质和精神,都将被救赎和被荣耀。
泽诺夫(Nicolas Zernov,1898-1980)对俄罗斯人的论述也适用于所有的正教徒,他说:
‘(圣像)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仅是绘画。它们动态地展现了人通过美和艺术,救赎受造物的精神力量。(圣像)的色彩和线条不是要模仿自然;艺术家的目的是展示人、动物、植物和整个宇宙能够从其目前的堕落状态中被拯救,恢复其真正的「形像」。(圣像)是被救赎的受造物将要战胜堕落的受造物的保证……圣像在艺术上的完美不仅反映出天上的荣耀——它也是物质恢复其原初和谐与美丽的具体例证,它充当了灵的载体。圣像是被改观的宇宙的一部分。’——《俄罗斯人及其教会》(The Russians and their Church )
如同大马士革的圣约安所说:
‘圣像是一首胜利之歌,是启示,是对圣徒之胜利及魔鬼之耻辱的不朽纪念碑。’ 《论圣像》
反圣像争论的终结,第七次大公会议的召开,正教会在843年的胜利——这些标志着正教历史第二阶段和七次大公会议时期的结束。这七次会议对于正教具有特别巨大的意义。对于正教会的成员来说,它们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还具有当代意义;它们不仅是学者和神职人员,还是所有信徒的关注点。斯坦利(Dean Stanley)说:“对于那些生活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目不识丁的农夫阶级来说,康斯坦斯(Constance)和特伦多(Trent)的名字或许闻所未闻,但它们知道他们的教会建立在七次大公会议的基础上,他们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第八次全体会议,时代的邪恶将会在那里被修正。”—《东方教会史演讲集》(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Eastern Church)
正教常常自称为"七次大公会议的教会"。这种称呼方式不意味着正教会自787年以来不再有创造性的思考。而是他们视大公会议时期为伟大的神学时代;七次会议被正教会视为仅次于圣经的标准和指引,并用于寻找答案以应对每一代都会遇到的新问题。
(四)圣人、修道士和皇帝
拜占庭被称为"天国耶路撒冷的形像"不是没有缘由的。宗教进入拜占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拜占庭的节日是宗教节日;竞技场里的比赛在开赛前都要歌唱赞美诗;商业契约要援引神圣三位一体并印上十字架的标记。在非神学化时代的今天,想到认识到社会中各个部分,平信徒或神职人员,穷人和目不识丁者或王室和学者,都对宗教问题报以如何狂热的兴趣,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尼撒的圣格里高利这样描述在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之时,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神学争论:
‘争论充斥于整个城市:广场、市场、十字路口、窄巷;衣衫破旧的人、货币兑换商、食品贩卖者都忙着争论。如果你要找人换零钱,他会就"受生和非受生"的问题做哲学讨论;如果你询问面包的价钱,答复会是"父高于子";如果你问"我的洗澡水准备好了吗?",伙计回答说"子是从无中被造出的"。’—《论圣子的天主性》(On the Deity of the son)
这种奇怪的抱怨表现出会议遭遇到的氛围。人们的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会议不是始终克制的或者有尊严的。
纳西昂的格里高利冷冰冰地说:“我在远处向会议致敬,因为我知道它们是多么烦人”,“我永远不会再和那些鹤与鹅聚坐在一起”。教父们有时运用令人质疑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例如,亚历山大的西里尔在同聂斯托利派斗争时,向宫廷贿赂重金,并动用由修士组成的私人军队威胁艾弗所城。可是如果说西里尔使用的方式过了头,这是因为他为了正当的目的而大发热心;如果说基督徒们有时尖酸刻薄,这是因为他们关心基督教信仰。秩序混乱也许比无动于衷更好。正教认识到与会者是不完美的人,但却相信这些不完美的人是受到了圣神的指引。
拜占庭主教不仅是出息会议的高高在上的人物,在许多情况下他还真是他的人民的父亲,是有困难之人的朋友和保护者,他们安心向他求救。约安.克里索斯顿表现出的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关怀,也可见于其他的许多人的身上。例如,亚历山大宗主教施舍者圣约安(St.John the Almsgiver,卒于619年),用教区内的所有财富帮助那些他称之为"我的兄弟和姐妹,穷人"的人。当他耗尽自己的资财,就向别人恳求,一位同时代的人记录说:“他常常说如果某人不是出于恶意,为了把衬衫给穷人穿上而把它从富人身上扒下,他没有错。”<施舍者约翰生平补遗>约安说:“那些被你们称为穷人和乞丐的人们,被我称为我的主和帮助者。因为他们,只有他们才能真正帮助我们,赐予我们天主的国。“拜占庭帝国的教会没有忽略其社会责任,它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慈善工作。
修道主义在拜占庭的宗教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它在所有正教国家都如此。“洞察正教神性传承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修道主义而进入正教"是一句公道的话。“在正教会的范围内,神性生活的形式丰富多样,但是修道主义在其中始终是最经典的。” 《东方宗教神秘神学》
在四世纪时,修道生活首次作为确定的制度出现在埃及和叙利亚,并从此处迅速传播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当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后,在迫害停止和基督教开始流行之时,修道主义应该立即发展起来,这不是巧合。苦修的修道士们是无流血的殉道者;他们构成了建制的基督教国中的抗衡力量。拜占庭社会中的人们面临着忘记拜占庭是一个形象和符号而非现实的危险,他们冒着将天主之国等同于尘世之国的风险。修士们通过撤离社会进入沙漠,在教会生活中实现预言和终末的圣职。他们提醒基督徒,上帝之国是不属于这个世上的。
修道主义采取了三种主要形式,这三种形式全都在公元350年前出现于埃及,并且现在仍然能在正教会中看到。
第一种是「隐士」,过着独居生活的禁欲者,生活在棚屋或洞穴中,甚至坟墓中,树杈间或柱子上。隐士生活的伟大榜样是修道主义之父,埃及的圣安当(St.Antony of Egygpt,251-356)。
第二种是「团体生活」,这里的修士们遵循共同的规则,一起居住在固定建好的修道院里。这种形式的伟大先驱者是埃及的圣帕克米(St.Pachomius of Egypt,286-346),他制定的规则后来在西方被圣本笃(St.Benedict)采用。圣大巴西略强烈倡导团体生活,他的禁欲主义著作对东方修道主义具有规范性的影响,虽然叙利亚对他的影响可能要比他曾经访问过的帕克米修道院(Pachomian Houses)要大。他主张修道主义要关注社会,敦促宗教团体应该关心弱者和穷人,开办医院和孤儿院,造福整个社会。但是从总体上说,东方修道主义远不如西部那样关注主动性的工作;正教修士的首要工作是祷告生活,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服务他人。对修士来说,攸关重要的,与其说是他"做了"什么,不如说是他"是"什么。
最后一种,是介于两种形式之间的半隐士的生活,这种中间方式不是单一的高度组织化的团体,而是由小的定居点松散连接成的团体,每个定居点可能有2至6名成员,在一位长老的指导下共同生活。埃及的半修道生活的伟大中心是尼帝亚(Nitria)和赛提斯(Scetis),到四世纪末时那里已经培养出许多杰出的修士:尼提亚的创建者亚门(Ammon the founder of Nitria),埃及的马喀里(Macarius of Egypt),亚历山大的马喀里(Macarius of Alexander)、本都的伊瓦格里乌(Evagrius of Pontus)、大阿森乌尼(Arsenius the great)。(这个半隐修士的制度不但见于东方,还可见于远西地区和凯尔特基督教中。)修道生活自一开始就存在于东方和西方,既是男人也是女人的天职,无数的修女团体遍及拜占庭世界。
4世纪的埃及凭借其修道院而被视为第二圣地,前往耶路撒冷的旅行者认为,除非他们探访尼罗河畔的苦修精舍,否则他们的朝圣之旅是不完整的。修道运动的领导权在5世纪和6世纪时转移到了巴勒斯坦,那里有大优锡米乌(Euthymius the Great,卒于473年)和他的学生圣萨巴斯(St.Sabas,卒于532年)。
圣萨巴斯在约旦山谷建立起来的修道院延续至今,从未间断;大马士革的圣约安就属于这个团体。另一个差不多同样古老的重要修道院也延续至今,不曾间断,它就是西奈山上的圣凯瑟琳(St.Catherine)修道院,创建者是查士丁尼皇帝(527-565年在位)。随着巴勒斯坦和西奈落入阿拉伯人之手,拜占庭帝国内的杰出修士在9世纪转入君士坦丁堡的修道院中。圣西奥多在799年成为修道院的院长,他使修道团体重新焕发生机,重新制定了修道规则,吸引了大批修士。
自10世纪以来,阿索斯(Athos)就成为正教修道运动的主要中心,这个由岩石构成的半岛在希腊北部延伸入爱琴海中,最高峰有6670英尺。作为众所周知的"圣山”,阿索斯包含20所"主管"修道院和许多小的修道院,以及隐士居住的洞穴;整个半岛完全作为修道者定居之用,据说在其全盛时期,阿索斯圣山拥有将近4万名修士。
大劳拉修道院(The Great Lavra)是20所主管修道院中最古老的一所,这一所修道院就培养出26位宗主教,至少144位主教,这说明了阿索斯圣山在正教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正教修道运动中并无「修会」。西方的修士属于加多森会(Carthusian)、熙笃会(Cistercian)或者其他修会;东方的修士却是包含一切修士和修女的伟大团体中的一员,虽然他们的确隶属于某一特定的修道院。西方的作家有时称正教的修士为"巴西略会修士”,但这是错误的。圣大巴西略是正教会修道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但是他没有创立修会,虽然他的两部作品《长规则》(Longer rules)和《短规则》(Shorter Rules)为人所知,但是它们不能同圣本笃的《会规》(Rules)相提并论。
正教修道运动中的独特人物是「长老」(希腊文geron,俄文starets,复数startsy)。长老是一种富有灵性洞察力和智慧的修士,无论是修士还是世俗中人都视他们为向导和神性导师。他们有时会是神父,但常常是非神职修士;他们承担长老的工作而没有受到专门的按立和任命,但是却受到了圣灵的直接感动而承担此项工作。
女性同男性一样担当此"圣职”,因为正教会有"灵性父亲"也有"灵性母亲"。长老以一种具体和实际的方式,在同每个前来向他们求教的人的关系中。洞察上主的意志,这是长老的特殊天赋或灵性之能(charisma)
最早和最著名的修道长老是圣安当本人。他在18至55岁的人生第一阶段,过着隐退和独居的生活;在其后,他仍然居住在沙漠中,但却放弃了先前严格的封闭式生活,开始接待访问者。在他身边聚集起一群学生,除了学生以外还有人数更多的,通常是来自于远方的一群人向他寻求建议;访问者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圣安当的传记作家阿塔纳修斯写道,他成了全埃及的医生。圣安当的后继者人数众多,其中的大部分人也遵循同样的外向活动模式——“为了重返而退离”。修士必须首先退离,必须在沉默中获得关于自己和天主的真理。在经过长期而严格的独居生活的准备阶段后,修士获得了长老所必需的洞察天赋后,就能够打开洞穴的大门,进入他先前逃离的这个世界。
拜占庭的基督教政治的心脏是皇帝,他不是普通的统治者,而是上主在世上的代表者。如果拜占庭是天国耶路撒冷的偶像,那么地上皇帝君主制就是天国的上帝君主制的图像;人们在教会中拜倒在基督圣像之前,在宫殿中拜倒在上帝的活生生的形像——皇帝 之前。迷宫一般的宫殿,繁文缛节的宫廷,王座宝殿礼雄狮呆板的吼叫和小鸟悦耳的歌唱:涉及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彰显皇帝作为上帝代理人的身份。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根尼图斯(Constantine Ⅶ Porphyrogenitus)皇帝这样写道:“我们体会到造物主天主在宇宙的和谐运作,帝国权力妥善有序地得到保存。”
皇帝在教会礼仪中享有特殊地位:他当然不能支持圣餐,但是他在教堂中"像神父那样"接受圣体血礼——手拿被圣化的饼,喝圣爵中的酒,而不是领受圣匙中的圣体血——他也讲道并在某些节日中为圣壇焚香。正教主教现在穿着的法衣就是皇帝曾经穿过的法衣。
拜占庭的生活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宗教和世俗,教会和国家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界限,两者都被视为一种有机体的部分。因此皇帝必然在教会生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但与此同时,把拜占庭称作皇帝教宗主义(Caesaro-Papism),教会附属于国家是不公正的。
虽然教会和国家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有机体,但是在这一个有机体内有两个不同的部分,圣职(Sacerdotium)和王权(Imperium);虽然这两部分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但是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在其中发挥自动性的恰切领域。两部分之间有着"和声"或"和谐",但是哪个部分都不能对另一部分实施绝对的控制权。
查士丁尼统治时代制定的拜占庭法典(见第六新律)详细阐释了这个教义,拜占庭的其他许多文本也重复了这条教义。例如皇帝约安.提米斯(John Tzimisces)曾说:“我认识两个权威,圣职和帝国;世界的创造者委托前者照料灵魂,委托后者控制人们的身体。不能让任何一个权威受到攻击,世界会享受繁荣昌盛”。因此皇帝有责任召开会议并实施会议决议,但是决定其决议的内容就是越权:只有参加会议的主教才能决定真正的真理是什么。上帝任命主教去教授真理,而皇帝则是正教的保卫者,而非正教的阐释者。理论上是如此,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不可否认,皇帝不合法干涉教会事务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当重要的原则问题出现时,教会权威会迅速表明他们具有自己的意志。例如,整整一系列的皇帝都大力支持破除圣像运动,尽管如此,教会却成功地拒绝了它。在拜占庭历史上,教会和国家有着紧密的互相依赖关系,但是任一方都不从属于另一方。
今天,正教会内外都有许多人尖锐批评拜占庭帝国和它所承担的基督教社会的理想。拜占庭人是大错特错吗?他们相信,当基督作为人在地上时,已经救赎了人类存在的每个方面,他们相信,洗礼的可能对象不但有个体的人,还有整个灵魂和社会组织。所以他们努力创造出在治理原则和日常生活方面完全基督教化的政体。拜占庭其实完全是在尝试接受和运用道成肉身的丰富含义。这种尝试一定有其危险之处:特别是拜占庭人常常错误地把地上的拜占庭王国等同于上帝之国,把希腊人——宁或说是"罗马人",他们自己使用这个词语表达他们自己的身份——等同于上帝的子民。拜占庭确实远远未及它自己树立的高尚理想,它的失败常常令人惋惜并具有灾难性。拜占庭的欺诈、暴力和残酷的故事太为人熟知,这里无需赘述。它们是真实的——但这些都仅仅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因为在拜占庭所有缺陷的背后,仍能感知到伟大的景象激励了拜占庭人:在世间建立一个活生生的形像,上帝在天国治理的形像。
第三章 拜占庭之二 :大分裂
我们是不变的;我们仍然是8世纪时的我们……多么希望你们能够同意再次成为你们曾经之所是,我们那时在信仰和团契中合一!——科米亚科夫(Alexis Khomiak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