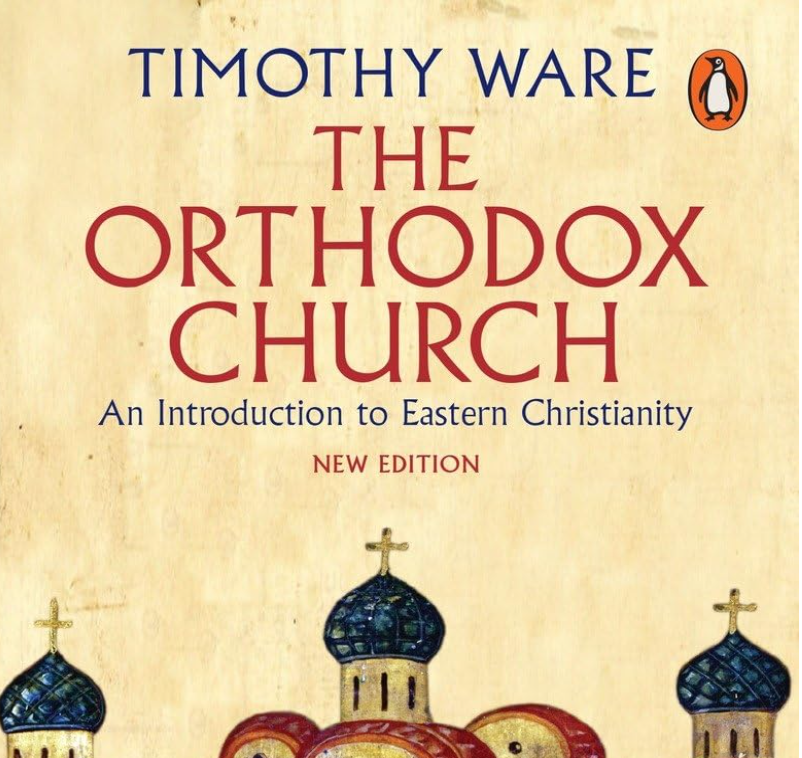-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课系列第六至七课,东西分开篇。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六课》,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9月6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 本讲稿由阿甲修订,很多内容参考这个中译本。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论》,中译田原(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若无特别说明,文字均是维尔主教的中译。若有阿甲的按语,则会写上:“阿甲按”三个字,并以引用符号标出。此篇以体现维尔主教著作为主,若要听阿甲的评论,请听讲座。
正文
阿甲按:拜占庭的正教关系模式是怎样的?
拜占庭东正教来说,政治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分开或融合的问题,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这是维尔主教对拜占庭时期东正教的看法。但对于现代社会,我们经常谈论的一个概念是政教分离的原则,有时也叫“政教分治”的原则,这似乎源自加尔文传统。但这并不是东正教会所拥有的一个政教关系的传统。东正教没有把教会和政治分得那么开。甚至维尔主教在这里说了一句话,表明在宗教与世俗、教会与国家的政治之间,并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界限。这是东正教政教关系的一个特点。而所谓的政教分治,其实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现代国家政体,比如欧美的民主政体,而在民主政体之前,英国也是基督教国家,更类似于拜占庭传统,那时的王室是赞助和保护基督教的。这些传统在女皇伊丽莎白时期也有所体现,她是一个基督徒,有时会在圣诞节发表一些声明或公告,表达对上帝的感谢,或者教导人们。但现在的国家并非如此,尤其是现在的美国和欧洲。我有一次在暑假期间,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有一些来自美国南卡的宣教师来皇上教会进行宣教活动。我就询问了有关今年美国大选的情况。这个基督徒说:“我没得选。我们只能选川普。”然后,他说到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民主党是敌基督的。”就是这样直接地说的。在他看来,民主党就是敌基督的。他们就是要破坏美国的基督教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在欧美被称为“左”的派别,基本上致力于铲除这些传统。维尔主教继续说,教会和国家形成一个单一的组织。然而,在这个统一的组织中,存在两个不同的元素:祭司阶层和皇权。也就是说,虽然政治与教会是一个整体,但在这一统一体内,在紧密合作中各自有其恰当的领域,这表明它们是一种合作关系。每一个元素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完成应该做的事情。在这两者之间,有交响乐般的和谐。这两种元素并没有绝对地控制对方。也就是说,在这种合作关系中,他们之间有一种和谐一致。基本上,东正教既拒绝罗马教宗的权力高于帝王的说法,又拒绝了现今民主体制下政教分离「或分治」的说法。这一观点在《查士丁尼法典》中得到了阐述。这个原则在许多拜占庭文献中都有记载。他说,这一原则是通过拜占庭法律确立的,起源于六世纪的查士丁尼皇帝。此后,这一法律一直被拜占庭的法律文献所维护。据帝王约翰·基梅松说,他承认两个权威。世界之主将灵魂的照料托付给第一种权威,将人类身体的控制权交给第二种权威。这两种权威都不应受到攻击,以确保世界能够繁荣昌盛。他说,我承认存在两种权威。一种是神职的权力,另一种是帝王的职权。他们两个要合作。这样就会使这个国家兴盛。
阿甲按:如何处理教会权威与政权之间的张力?
在这里面后面也说了一段。虽然理想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但是在教会的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干涉教会内部事务的一些情况。帝王有时会干涉教会的事务,通过强力手段干涉教会事务的情况也存在。但是当涉及原则性问题时,教会的权威便会迅速上升,以表达其意志。这一点在后两次大公会议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尤其是在第七次和第六次大公会议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君王想通过自己的意志来主持一次大公会议,并将他对教义的看法「一志论」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在第六次东正教会议中,先出现了一位修士,名叫认信者马克西姆,他反对这一观点。到了第七次大公会议时,另一位修士,即大马士革的约翰来反对这个拆毁圣像的运动。在其中可以看到,教会它确实拥有一个平衡的力量。特别是在第六次和第七次大纲会议的时候,这是通过修道主义传统体现出来的。如果我们说东正教的教会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尤其体现在教义和礼仪上。教会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修院中实现的,简单来说,修院就像是教会中的精兵。
阿甲按:天主教有何优势?
在我的学习过程中,就翻译成就而言,拉丁文的译本要比希腊文的译本多。因为很少有希腊人会从拉丁语翻译过来希腊文的译本。然而,许多文献是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的。这种现象当然有其原因:因为早期有许多希腊文著作被译成了拉丁文。这是因为圣经并非用希腊文书写而成的。在此方面,我必须赞扬天主教徒,尤其是早期说拉丁语的基督徒,他们热衷于翻译希腊文作品。只要有名的希腊文作品,就一定会被翻译过来。早期在五十纪、六十纪甚至到七十纪时,他们并不缺乏能够将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的专家。但是,在同一时期的希腊教父们却很少见到。他们可以阅读拉丁文,或者愿意阅读拉丁教父的著作。至少在我的有限了解内没有这种情况。所以你可以在这一点上看出,希腊人有一种民族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使用的是希腊语,而圣经也是用希腊语写的。既然我们已经拥有这些用希腊语写成的作品,为什么还要翻译其他语言的著作呢?早期从拉丁文译成希腊文的作品,我所知有限,只有卡西安的作品被译成了希腊文,其他的翻译资料,很少见。比如说,你研究奥利金,必须学习拉丁文,因为大多数能找到的译本都是拉丁文的。相比之下,希腊文版本则较少见,因为奥利金被定为异端后,其希腊著作就被销毁了,或者只能以匿名的方式保存下来。
第三章 拜占庭之二 :大分裂
我们是不变的;我们仍然是8世纪时的我们……多么希望你们能够同意再次成为你们曾经之所是,我们那时在信仰和团契中合一!——科米亚科夫(Alexis Khomiakov)
(一) 东方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疏远
在1054年的一个夏日午后,当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教堂正要开始进行事奉礼仪的时候,枢机主教洪波特(Cardinal Humbert)和另外两位教廷使节走进圣堂中。他们不是来祈祷的。他们把一张逐出教会的教宗诏书放到圣坛上,又走了出去。当枢机主教走过西门时,他抖掉脚上的灰尘,说着:“让上帝去看和裁决吧!",一位执事跑出去追他,这位执事非常悲痛,乞求他收回教宗诏书。洪波特拒绝了;诏书被扔到大街上。
按照惯例,这一事件标志着正教东方与拉丁西方之间大分裂的开始。但是现在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大分裂事件的开始日期不能精确地被确定。大分裂的来临是渐进的,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的结果,它在11世纪开始之前发生,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仍未结束。
在这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许多不同的影响力量发挥了作用。大分裂受到文化、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作用,可是其基本原因并非是世俗的,而是神学上的。东西方最后是关于教义的问题进行争吵,特别是在关于教宗主张与「和子」(filioque)这两个问题上。但是我们在更详细地考察双方的主要区别之前,在考虑大分裂的实际进程之前,必须介绍更广阔的背景。在东西方之间发生公开而正式的大分裂很久以前,双方就开始互为陌生人;在试图理解基督教世界的共融如何与为何分裂之前,我们必须从这个渐行渐远的事件的发展开始入手。
当圣保罗和其他的宗徒环绕着地中海世界旅行的时候,他们是在罗马帝国这个有着紧密的政治和文化联系的统一体内行走。这个帝国包含许多不同的民族团体,他们常常具有各自的语言和方言。但是所有这些团体都被同一个皇帝统治,博大的希腊文明为帝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所享有的;帝国各处的人们几乎都能听懂希腊语或拉丁语,许多人能讲两种语言。这些事实对早期教会进行福传工作有极大的裨益。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地中海世界的统一逐渐消失了。首先消失的是政治统一体。自从3世纪末期以来,帝国虽然在理论上仍然是统一的,但是分裂成为东方和西方两部分,每部分都有各自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通过在东方建立帝国的第二都城,与意大利的旧罗马相并列的都城,推进了这一分裂过程。 在5世纪开始时,出现了蛮族的入侵,除了意大利以外,西方被蛮族首领瓜分殆尽,意大利的大片领土在较长的时期内仍保留在帝国内。拜占庭人从未忘记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统治时的罗马理想,仍然认为他们的帝国在理论上是统一的;但是查士丁尼是认真地尝试在理论和现实之间架设桥梁的最后一位皇帝,他不久就放弃在西方的征战。蛮族的入侵摧毁了说希腊语的东方和讲拉丁语的西方的政治统一体,并且永远都未恢复起来。
在6世纪晚期和7世纪,阿瓦人(Avar)和斯拉夫人入侵巴尔干半岛,这加深了东方和西方的互相孤立,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曾充当桥梁的伊利里库姆(Illyricum)成了拜占庭和拉丁世界之间的屏障。伊斯兰教的兴起继续使分离延续,地中海一度被罗马人称为mare nostrum,我们的海,现在则主要落入了阿拉伯人之手、地中海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文化和经济接触从未完全消失,但是变得愈加困难。
反圣像争论对于拜占庭和西方之间的分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教宗坚定地支持偶像崇拜论的立场,因此他们发现自己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同君士坦丁堡的反圣像的皇帝和宗主教失去了共契。教宗斯蒂芬(Stephen)受到拜占庭的孤立而需要帮助,他在754年向北方求助,访问了法兰克人的统治者佩金(Pepin)。就罗马教廷而言,这标志着决定性的方向转换的第一步。迄今为止,罗马在很多方面仍然是拜占庭世界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它逐渐地接受法兰克人的影响,虽然这一重新转向的结果直到11世纪中期才变得完全明朗。
在教宗斯蒂芬访问佩金半个世纪以后,一件更加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了。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宗利奥三世(Leo Ⅲ)为法兰克人的皇帝,查理大帝加冕称帝。查理曼曾经寻求拜占庭统治者的认可,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拜占庭人仍然坚持帝国统一的原则,认为查理曼是入侵者,教宗为他举行的加冕仪式是分裂帝国的举动。神圣罗马帝国在西方的创建,并没有使欧洲变得更加凝聚,只是使东方和西方的疏远较以往更为严重。
文化统一体继续保留着,但是却采取了一种非常微弱的形式。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有教养的人仍然生活在古典的传统之中,这个传统被教会所接管并被教会据为己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开始以日渐相异的方式解释这一传统。语言的问题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受教育的人说双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到了450年,西欧很少有人能读懂希腊文,在600年以后虽然拜占庭仍然自称是罗马帝国,但是拜占庭人很少讲罗马人的语言——拉丁语。9世纪君士坦丁堡最伟大的学者圣大弗提乌斯(Photius)不能阅读拉丁语,在864年,拜占庭的一位"罗马"皇帝麦克三世(Micheal Ⅲ)甚至称维吉尔(Virgil)的写作用语为"蛮族和赛斯人(Scythic)的语言”。如果只懂希腊文或者拉丁文的人士想要阅读对方语言的著作,就只能阅读翻译本,通常他们不在这方面花费力气:赛鲁斯(Psellus)是11世纪时的一位博学的希腊学者,他的拉丁文献知识却是如此贫瘠,以致于把凯撒(Caesar)混淆为西塞罗 (Cicero)。因为他们不再使用相同的文献,也不再阅读相同的书籍,讲希腊语的东方和拉丁语的西方渐行渐远。
查理曼宫廷的文化复兴自一开始就打上了强烈的反希腊的偏见的印记,这是一个不详但却重要的先例。欧洲在4世纪时就有一个基督教文明,在13世纪时有两个基督教文明。也许在查理曼统治时期,两个文明的分裂第一次变得清晰醒目。拜占庭人在他们自己的思想世界里徜徉,没有在半路上遇见西方。在9世纪和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拜占庭人也常常不能认真对待西方的知识。他们把所有法兰克人都当做蛮族予以遣散。
这些政治和文化因素不能不影响教会生活,使教会更难以维持宗教统一。文化和政治上的疏远容易导致教会争端,从查理曼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拜占庭皇帝拒绝承认查理曼的政治地位,查理曼被指控为脱离拜占庭教会的异端,他很快对这一指控做出报复:他指责希腊人在信经中不使用「和子句」(我们稍后将详细论及此点),他拒绝接受第七次大公会议的决定。真实情况是,查理曼通过一个严重歪曲原意的错误译本才知道这些决定,但是无论如何他的观点看上去都是半反偶像的。
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政治环境使教会具有不同的外在形式,所以人们渐渐以互相冲突的方式理解教会的教令。自一开始,东方和西方的着重点就有一定的差异。在东方,许多教会的基础都可以追溯至宗徒,所有主教都有着强烈的平等意识,教会具有法团和会议的特性。东方认为教宗是教会的首席主教,但是把他视为平等者中的首席。另一方面,在西方只有一个大主教教区——罗马——声称具有唯一宗徒传承的基础,罗马因此被视作是宗徒教区。虽然西方接受了大公会议的决定,但是自己却不在会议中发挥积极作用,与其说教会被视为法团,不如说是被视为君主国——教宗的君主国。
这个最初的观点分歧由于政治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尖锐。蛮族的入侵,随后帝国在西方的瓦解自然极大地强化了西方教会的专治结构。在东方,有一个强大的世俗首领——皇帝,支持文明的秩序并实施法律。在西方,当蛮族到来后,只有许多战争首领,所有首领或多或少都是篡位者。能够担当统一体中心的,能够在西欧的灵性和政治生活中担当连续而稳定元素的,主要是罗马教廷。借助环境的力量,教宗担任的角色是希腊宗主教不曾担当的,他不但向教会中的下级还向世俗统治者发布命令。西方教会的集权化逐渐发展,达到了东方四个宗主教区(可能出了埃及外)闻所未闻的程度。西方实行君主制,东方实行共同掌权制(collegiality)
蛮族入侵给教会生活带来的影响还不止于此。拜占庭有许多有教养的平信徒对神学有积极的兴趣。“平信徒神学家"始终是被正教接受的人物。一些最博学的拜占庭宗主教在接受宗主教职任命以前都是平信徒,例如圣大弗提乌斯(Photius the Great)。但是在西方,教会为其神职人员提供的教育是黑暗时代中唯一能够存活的有效教育。神学变成神父们的保留项目,因为大多数平信徒甚至不能阅读,遑论理解神学讨论的专业术语。正教虽然赋予主教特殊的教育职责,但从未闻知神职人员与平信徒之间的差距竟如此显著,这种差别出现在西方中世纪时期。
由于缺乏共同语言,东方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同对方的交流不再容易,每一方都不在能够阅读另一方的文字,误解更容易出现了。共享的"论域"逐渐消失了。
东方和西方变得互相陌生,双方都从中受难。早期教会虽然有多重神学学派,但却有统一的信仰。希腊人和拉丁人自一开始就在各自的道路上接近基督教的神秘。下述说法有过于简单化的危险:拉丁人的进路更具实践性,希腊人的进路更富冥想性;拉丁人的思想受到法律思想和罗马法观念的影响,而希腊人则是在礼仪敬拜的背景下,依照圣礼理解神学。在思考神圣三位一体时,拉丁人从一个神性开始,希腊人从三个位格开始;在思考十字架受难时,拉丁人首先想到基督是受难者,希腊人则认为基督是胜利者;拉丁人更多地讨论救赎,希腊人喜欢讨论圣化;等等。如同东方的安提阿学派和亚历山大学派一样,这两个不同的进路本身也不是互相冲突的;每个都是另一个的补充,每个都在完整的公教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双方现在变得互相陌生——没有政治上的统一,没有共同的语言,只有文化上的些微统一——每一方都面临着孤立地遵循各自进路和走向极端的危险,忘记了另一方观点的价值。
我们已经说到东方和西方具有不同的教义进路,但是在「教宗首席权」和「和子句」这两点教义上,双方却不再互补,而是进入了直接的冲突之中。我们再前述段落中提到过的因素,足以对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形成沉重的压力。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东西方之间或许仍然维持着统一。我们现在必须探讨这两个问题。完全的分歧直道9世纪中期才首次正式公开,但是这两个教义分歧的起源却相当早。
当我们讲到东方和西方具有不同的政治环境时,已经提到过教宗首席权,我们已经看到蛮族的入侵是如何强化了西方教会的集权制和君主制结构。现在,只要教宗在西方要求具有绝对的权力,拜占庭就不会提出反对。只要教宗的权力不干涉东方,拜占庭人就不介意西方教会是否集权化。然而,教宗相信他对西方和东方都具有直接的管理权,只要他试图在东方宗主教区运用这项权力,麻烦必定出现。希腊人授予教宗以最高的荣誉,而非教宗想当然的普世至尊权。教宗认为绝对无谬误性是他自己的特权,希腊人认为信仰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不为教宗独有,而为代表教会全体主教的会议所有。我们有了两种关于教会可见组织的不同观念。
12世纪的一位作家尼塞塔斯(Nicetas)是尼科米迪亚(Nicomedia)的枢机主教,他的一段话绝好地表达出正教对于教宗首席权的态度:
‘我最亲爱的兄弟,我们不否认罗马教会在五个姐妹宗主教区中居于首位,我们承认她在大公会议中享有位居最尊贵坐席的权利。但是她自己的行为却使她同我们相分离,她骄傲地呈现出本不属于其职权的君主制……她不同我们商议甚至不知会我们,就对我们发出命令,我们怎能接受这样的命令?坐在高耸的荣耀王座里的教宗,如果想对我们大发雷霆,在高处把命令掷给我们,如果他不同我们商量而是肆意评判我们,甚至想要统治我们和我们的教会,这是什么样的手足情谊,他又是如何为人父母的呢?有了这样的教会,我们就会是他的奴隶而非儿子,罗马教区不会是儿子们的虔诚母亲,而是奴隶们铁石心肠的奴隶主和飞扬跋扈的情妇。’——《东部的分裂》(The Eastern Schism),S.Runciman
当整个问题公开时,12世纪时的正教徒有了如上的感受。在前几个世纪中,希腊人对待教宗首席权的态度基本相同,但态度尚未被争端所激化。在850年以前,罗马和东方在教宗首席权的问题上避免公开冲突,但是观点分歧并没有由于部分地掩饰而得到缓和。
第二个大难题是「和子句」。《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中关于圣灵的词语引起了这场争论。信经最初写道:“我相信……圣灵、主、生命的赐予者,祂源出于父,祂同父和子一道被崇拜和被荣耀。“迄今为止,东方一直原封不动地引述这个最初的表述。但是西方另加了一句"和源出于子”(拉丁文Filioque),所以信经现在的写法是"祂源出于父和子”
不清楚这个附加词第一次在何时何地出现,但它似乎源于西班牙,是为了反对阿里乌主义(Arianism)。如果不是更早,就在第三次托莱多(Toledo)宗教会议(589年)上,西班牙教会加入了「和子」。这一附加词从西班牙开始传播到法兰西,然后传播到德国,在那里受到查理曼的欢迎,被法兰克福的半反偶像会议(semi-Iconoclast)(794年)所采用。查理曼宫廷的作家们首次使「和子」成为争议问题,希腊人由于引述最初的信经而被指控为异端。但是罗马采取了典型的保守主义立场,在11世纪开始以前一直使用没有「和子句」的信经。808年教宗良利奥三世在一封写给查理曼的信中说,虽然他本人相信「和子句」在信理上是合理的,但是他认为篡改信经的字句是错误的。利奥三世有意让人把没有「和子句」的信经刻在银质铭牌上,悬挂在圣彼得大殿里。此时的罗马在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之间充当调停人的角色。
希腊人直道850年才开始非常重视「和子句」,但是一旦他们重视起来,他们的反映是尖锐苛刻的。正教反对(现在仍然反对)给信经添加附加词的理由有两个。首先,信经是整个教会的共同财产,只有经过大公会议的同意,才能对信经做出修改。西方没有同东方商议就修改信经,(就像科米亚科夫所说)犯了道德上的弑兄之罪,是违反教会统一之罪。其次,大多数正教徒相信「和子句」在信理上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圣灵只源出于圣父,如果说祂也源出于圣子就是异端。可是,一些正教徒认为「和子」本身不是异端观点,可以真正作为一种神学观点——而非教义——而被采纳,条件是它能够得到正确的解释。但即便是这些采取更温和立场的人仍然认为「和子」是没有经过授权的附加词。
除了「教宗首席权」和「和子句」这两个主要问题,还有教会崇拜和纪律等次要问题引发东西方之间的争论,希腊人允许神职人员结婚,拉丁人坚持神父过独身生活;双方有不同的斋戒规则;希腊人在圣体血圣事中使用发酵饼,拉丁人使用未经发酵的饼或"无酵饼”。
东方和西方在850年左右时仍然有完全的共契,仍然形成统一的教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分隔共同导致疏远日益增长,但此时没发生公开的分裂。双方对于教宗权柄有不同的理解,使用不同的方式引述信经,但这些问题尚未完全公开。
但是在1190年,安提阿宗主教和伟大的教会法权威西奥多.巴尔萨蒙(Theodore Balsamon)在看待这些问题时,采取了极为不同的观点:
‘数年以来(他没说多少年),西方教会同其他四个宗主教区之间的灵性联系已经隔断了,已经同正教相疏远……只有拉丁人首先宣布放弃那些使他们同我们相隔断的教义和习俗,并受制于教会法规,(他们)才能恢复同正教的共契和联合。’ 《东部的分裂》
在巴尔萨蒙的眼中,共契被打破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分裂是确定的。双方不再构成一个可见的教会。
在从疏远到分裂的变迁中,有四件事的意义特别重要:
圣大弗提乌斯和教宗尼古拉一世(Nicolas Ⅰ)之间的争吵(通常被称为"弗提乌斯分裂");1009年的折合书(Diptychs)事件;1053至1054年的和解尝试及其灾难性的结果;十字军东征。
(二) 从疏远到分裂:858年至1204年
在狄奥多拉(Theodora)统治时的圣像运动胜利以后15年,也就是858年,一位新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弗提乌斯被任命,正教会称其为伟大的圣弗提乌斯。他被视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中最杰出的思想家,最卓越的政治家和最娴熟的外交家"—《拜占庭国家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在他就任宗主教后不久,就卷入了一场同教宗尼古拉一世(Nicolas Ⅰ)的争论中。上一位宗主教圣伊格纳修(St.Ignatius)遭到皇帝的流放,在流放期间迫于压力而辞职。圣伊格纳修的支持者们拒绝承认辞呈是合法的,认为圣弗提乌斯是篡位者。当圣弗提乌斯给教宗写信宣布自己的就任时,尼古拉决定在承认圣弗提乌斯以前,要进一步观察新宗主教和伊格纳修追随派之间的斗争。
因此在861年,他派使节出访君士坦丁堡,圣弗提乌斯不想发起同教宗的争论。他以大礼对待使节,邀请他们在君士坦丁堡主持一场会议,旨在解决圣伊格纳修和自己之间问题的会议。使节们和其余的会议成员一致决定圣弗提乌斯是合法的宗主教。但是当使节们回到罗马以后,尼古拉宣布他们越出了他们的权限,他推翻了他们的决定。然后他亲自在罗马继续重判这个问题:他在863年主持的一场会议中认定圣伊格纳修是合法宗主教,宣布免除圣弗提乌斯的一切教牧尊严。拜占庭人没有注意到这项谴责,没有回复教宗的信件。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裂痕公开出现了。
这场争论显然涉及教宗权柄。尼古拉是一位伟大的改革派教宗,得意地认为他的主教辖区享有诸多特权,他为了建立超越所有主教的绝对权力,在西方着力甚多。但是他相信这种绝对权力也应该扩展到东方,他在865年写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教宗被赋予了"超出全世界,即超出一切教会"的权威。这恰恰是拜占庭人不准备承认的。
面对圣弗提乌斯和圣伊格纳修的争斗,尼古拉认为他看到了一个实现其普世管理权的绝佳机会,他要使双方都承认他的裁决。但是他意识到圣弗提乌斯已经自愿的接受了教廷使节的调查,这个行动不意味着承认教宗的至尊地位。这(还有其他原因)是尼古拉之所以废除使节的决定的原因。
对于拜占庭人来说,他们愿意向罗马上诉,但这只是在萨迪卡(Sardica)宗教会议(343年)的第三条教规规定的特殊情况下。这条教规规定,如果主教被定罪,他能够向罗马和教宗上诉;如果教宗理解诉讼的原因,就能命令重审(案件);然而,进行重审的不是罗马的教宗本人,而是被定罪主教的临近省区的主教们。教宗尼古拉推翻了他的使节们的决定并要求由他本人在罗马重新审定,拜占庭人认为这违反了教规的规定。他们认为他的行为是没有根据的和不合教规的,干涉了其他宗主教区的事务。
除了教宗权柄,「和子句」不久也被牵涉进争论中。拜占庭和西方(主要是日耳曼人)都对斯拉夫人发起了伟大的福传冒险。东线和西线的两路传教士向前推进,很快便汇合了;当希腊人和日耳曼人传教士发现他们自己在同一片土地上工作时,冲突难以避免,因为两个传教团依据极其不同的原则运作。冲突自然地将「和子句」推向前台。日耳曼人使用的信经里有「和子句」,而希腊人的信经里没有。主要的困扰焦点是保加利亚,罗马和君士坦丁堡都急于把该国拉入其管理范围之中。鲍里斯(Boris)可汗起初倾向于请日耳曼传教士进行洗礼,但是由于受到拜占庭入侵的威胁,他改变了政策,大约在865年接受了希腊神职人员的洗礼。
但是鲍里斯想要保持保加利亚教会的独立,当君士坦丁堡拒绝给与自治权后,他转向西方,希望得到更好的条件。拉丁传教士被允许在保加利亚放手开创事业,他们立即对希腊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列出了拜占庭与自己在实践方面的不同之处:已婚的神职人员,斋戒规则,最重要的是「和子句」。罗马自己仍然没有使用「和子句」,但是当日耳曼人在保加利亚坚持加入「和子句」时,教宗尼古拉对日耳曼人予以全力的支持。于808年在法兰克人和希腊人之间进行调停的教宗权威现在不再中立了。
日耳曼人恰好在拜占庭帝国边界上与巴尔干人中扩展势力,这自然使圣弗提乌斯惊恐不安,但是现在强行进入其视线的「和子句」的问题使他更惊慌失措。他在867年采取行动。他写了一份通谕致东方的其他宗主教,详细地谴责了「和子句」。指控那些使用「和子句」的人是异端。圣弗提乌斯常常由于写这封信而备受指责:甚至连伟大的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方济各.德沃尼克(Francis Dvornik),虽然在总体上非常同情圣弗提乌斯,都认为他在这种情况下的行动是"无效的进攻",还说"轻率仓促的失误,重大的致命结果"—《弗提乌斯分裂》(The Photian Schism)。
但是如果圣弗提乌斯真的认为「和子句」属于异端,除了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还能做什么呢?必须谨记,首先使「和子句」成为争议的不是圣弗提乌斯,而是70年前的查理曼和他的学者们,最初的挑衅者是西方,而非东方。圣弗提乌斯写完信后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宣布教宗尼古拉被逐出教会,称其为"毁坏了主的葡萄园的异端"。
这场争论的关键时刻,整个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在同一年(867年),皇帝罢免了圣弗提乌斯的宗主教职位。圣伊格纳修再次成为宗主教,恢复了同罗马的联系。在869至870年,另一场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召开,此即所谓的「反弗提乌斯会议」,会议谴责和绝罚了圣弗提乌斯,推翻了867年的决定。这次会议后来被西方认定为第八次大公会议,开始时总共有12位不甚引人注目的主教参加,在其后的会议上与会的主教人数升至103位。
但是进一步的变化出现了。869至870年的会议要求皇帝解决保加利亚教会的地位问题,他决定保加利亚应被划入君士坦丁堡主教区,这一点也不奇怪。可汗鲍里斯认识到罗马给与的独立比拜占庭的独立更少,他接受了这个决定。于是,从870年开始,日耳曼人传教士被驱逐出去,在保加利亚境域内听不到「和子」了。
这并非全部。圣伊格纳修和圣弗提乌斯在君士坦丁堡实现和解了,当圣伊格纳修在877年去世时,圣弗提乌斯再一次接替他成为宗主教。另一场会议于879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有383位主教参加——同10年前的反弗提乌斯会议的寥寥参与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869年的会议受到强烈的谴责,对圣弗提乌斯的一切谴责都被撤回,罗马没有抗议,接受了这些决定。因此圣弗提乌斯在最后取胜了,得到罗马的承认,成为保加利亚的教会领袖,直到近来还有人认为出现过第二次"弗提乌斯分裂",但是德沃尼克博士的惊人结论已经证实了第二次分裂是一个"神话":在圣弗提乌斯在位的后期阶段(877-886),君士坦丁堡同罗马教廷之间的联系始终没有破裂。
此时的教宗若望八世(872-882)并非法兰克人的朋友,也没有在「和子句」的问题上进行逼迫,更没有尝试在东方坚持教宗权柄。也许他认识到了尼古拉的政策给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威胁。
因此分裂在外部得到治愈,但是由于尼古拉和圣弗提乌斯之间的争论而公开化的两个重大分歧,仍未得到真正的解决。事情已经得到平息,仅此而已。
东方一直将圣弗提乌斯尊奉为圣人、教会领袖、神学家,西方过去将其视为分裂的作俑者,对他不那么狂热。他的优秀品格现在得到更为广泛的欣赏。
德沃尼克博士的巨著结尾写到:“如果我的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再一次自由地认识到,弗提乌斯是伟大的教士,博学的人文主义者,是真正的基督徒,宽宏地原谅他的敌人,走出了迈向和解的第一步。” 《弗提乌斯分裂》(The Photian Schism)。
在11世纪开始时,关于「和子句」的新麻烦出现了。罗马教廷最终采用了这附加词:在1014年于罗马举行的亨利二世皇帝加冕仪式上,咏颂了篡改过的信经。在5年前的1009年,新当选的教宗塞吉乌斯四世(SsergiusⅣ )向君士坦丁堡发出的信件中可能已经包含了「和子句」,虽然这不确定。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也同名叫塞吉乌斯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没有在折合书中加上新教宗的名字。
每位宗主教都保留这些名单,上面写有他认为是正统的,活着的和已故的其他宗主教的名字。折合书是教会统一的有形标记,故意在上面漏掉一个人的名字等于宣布同他断绝关系。
过了1009年以后,教宗的名字还是没有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的折合书上,严格上说,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从那时起中断了联系,但是不能根据这个举动而下定论。折合书经常是不完全的(名单),因此不能绝对无误地显示教会的关系。1009年以前的君士坦丁堡名单常常缺漏教宗的名字,这只是因为新就任的教宗没有通知东方。1009年的缺漏没有引起罗马的评论,甚至连君士坦丁堡的人们也很快忘记折合书首次漏掉教宗的名字究竟出于何因,出现于何时。
在11世纪的推进过程中,新的因素加深了罗马教廷和东方宗主教区之间关系的危机。对于罗马教区来说,上个世纪是一个发生巨大动荡和混乱的时期,枢机主教巴罗尼乌斯(Baronius)公正地称那个世纪为罗马教廷历史上的铁和铅的时代。但是在日耳曼的影响下,罗马教廷进行自身改革,经过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教宗格里高利七世)等人的统治后,在西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地位。改革后的罗马教廷自然重新要求教宗尼古拉曾经提出的普世管理权。拜占庭人这一方已经惯于应对在大多数时候显得软弱和混乱的罗马教廷,因此他们发现自己现在难以适应新的形势。11和12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意大利受到诺曼人的军事入侵,地中海东方受到意大利沿海城市的商业侵蚀,诸如此类的政治因素使问题变得更糟。
一场严重的争吵在1054年爆发。诺曼人强迫拜占庭和意大利的希腊人遵守拉丁传统的习俗,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迈克尔.塞鲁拉里乌斯(Michael Cerularius)转而要求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会采取希腊教会的实践,当后者在1052年拒绝时,前者关闭了这些教会。这个做法也许是粗陋的,但是作为宗主教,他完全有权这样做。
在多重实践中,迈克尔及其支持者特别反对拉丁人在圣体血礼中使用无酵饼或未发酵的饼,这个问题在9世纪时没有引发争议。可是塞鲁拉里乌斯在1053年采取了更为调和性的态度,他写信给教宗利奥九世,提出在折合书上恢复教宗的名字。利奥九世回应了这个提议,为了解决希腊和拉丁习俗的争议问题,他在1054年派遣三名使节出访君士坦丁堡,使节首领是希尔瓦.坎迪那(Silva Candida)主教洪波特(Humbert)。
选择枢机主教洪波特是不幸的,因为他和宗主教塞鲁拉里乌斯两人都有着强硬和不妥协的脾气,他们相遇时不可能发扬基督徒之间的善意。当使节们拜访塞鲁拉里乌斯时,没有形成良好的印象。他们把教宗的信丢给他,没有正式行礼就退出了;信件的署名者虽然是教宗利奥九世,但真正的起草者却是洪波特,语气极为不友好。宗主教此后拒绝继续同使节打交道。最终洪波特失去耐心,在圣索菲亚大殿的圣坛上张贴了将塞鲁拉里乌斯绝罚的公告。
这份文件的指控毫无根据,洪波特指控希腊人在信经中漏掉「和子句」。洪波特没有进一步解释他的行为,马上离开了君士坦丁堡,他一回意大利,就说整个事件是罗马主教教区的重大胜利。塞鲁拉里乌斯和他的宗主教会议做出了报复,绝罚了洪波特(而非罗马教会本身)的教籍。这次和解的尝试反而恶化了与拉丁教会的关系。
但即使是在1054年以后,东西方之间仍然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基督教世界的两个部分尚未意识到将他们隔开的巨大鸿沟,双方的人们仍然希望不花太多力气就消除误解。这场争端仍然不为东方和西方的大多数普通基督徒所知。使分裂确定下来的,是十字军东征,它们引入了仇恨和痛苦的新精神,将整个问题带到大众层面。
然而,从军事视角来看,十字军东征在开始时取得了显赫的成功。安提阿在1098年被土耳其人攻克,耶路撒冷在1099年被攻克,第一次十字架东征虽然血腥,但是成就辉煌。
(阿吉里斯的雷蒙 Raymond of Argiles 写道:“在圣殿和所罗门的廊下,人们骑马穿行,血流没过膝盖和马匹龙头缰绳……城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引自A.C.Krey,《第一次十字军东征》The first Crusade)
十字军战士在安提阿和耶路撒冷让拉丁人当宗主教。在耶路撒冷,这合情合理,因为牧座当时空缺,虽然在其后的数年中,耶路撒冷的一系列宗主教在塞浦路斯过着流徙生活,但是巴勒斯坦城内包括希腊人和拉丁人在内的所有民众,起初都接受拉丁宗主教的领导。
俄罗斯车尼格夫的修道院长丹尼尔(Abbot Daniel of Tchernigov)于1106至1107年在耶路撒冷朝圣,他发现希腊人和拉丁人一起在圣地和谐地举行崇拜活动,虽然他满意地发现在圣火仪式上,希腊人的灯被神奇地点亮,而拉丁人点灯时不得不向希腊人借火。但是在安提阿,十字军战士发现一位希腊宗主教正在任上,真实情况是,他此后不久就撤回君士坦丁堡,但是当地的希腊民众不愿意承认十字军战士推选出的拉丁宗主教。所以自从1100年起,安提阿实际上出现了教会的分裂。
当萨拉丁(Saladin)在1187年攻克耶路撒冷后,圣地的形势恶化了:都在耶路撒冷定居的两个对手,阿雷克(Acre)的拉丁宗主教和耶路撒冷的希腊宗主教,现在将基督徒民众划分为两个部分。发生在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的地方性分裂让事态演变地更为恶劣。
罗马地处远方,如果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发生争论,对于叙利亚或者巴勒斯坦的普通基督徒来说,罗马能发挥什么实际作用?但是当争斗双方的主教都要获得同一个权位,而两派敌对的会众共存于同一个城市中时,分裂马上成为一个事实,单纯的信众直接涉入其中。
十字军东征使所有基督徒信友——而非仅仅是教会领袖——都牵涉到争论之中,十字军战士使分裂降到了地方的层次。
但是更糟的情况又在1204年出现,君士坦丁堡在第4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被攻克了。十字军的最初目标是埃及,但是受到被废黜的拜占庭皇帝伊萨克.安格鲁斯(Isaac Angelus)的儿子们阿里克西乌斯(Alexius)的规劝后,便转向耶路撒冷以恢复他们父子的王位。西方在干涉拜占庭政治时并非欢快顺畅,十字军最后被他们所认为的希腊式狡诈弄得烦不胜烦,失去了耐心,洗劫了这座城市。东方的基督教世界永远不会忘记那三天恐怖的劫掠。
尼西塔.卓尼塔(Nicetas Choniates)抗议说:“同那些肩负基督十字架的人相比,甚至连撒拉逊人都是仁慈和善的。“朗西曼(Steven Runciman)爵士说:“十字军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剑,将基督教世界割断。” <东部的分裂>
强烈的民族仇恨,西方入侵和亵渎引发的仇恨和愤慨的情感,增强了希腊与罗马在长期上教义的分歧。在1204年以后,东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无疑分裂成两部分了。
对于出现在他们当中的教义问题,正教和罗马都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对方是错误的,所以罗马和正教在分裂后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教会。每当双方坚持相信自己具有正当的缘由,也必须带着悲伤和忏悔回首往事。双方必须真挚地承认,他们本来能够和应当更有作为地防止教会分裂。双方都在人性层面上犯有过失。
例如,正教必须检讨自己在拜占庭时期对待西方时的傲慢与轻蔑,检讨自己在1182年暴乱等事件中的过失,当时君士坦丁堡的许多拉丁人居民遭到拜占庭民众的屠杀。(拜占庭一方依然没有任何行动可与1204年的洗劫相提并论。)虽然双方都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教会,但却必须承认分裂使人类处于严重的贫困之中。东方的希腊人和西方的拉丁人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对方。大分裂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悲剧。
(三) 再联合的两个尝试;静修士的争议
当希腊人在1261年光复首都之后,十字军1204年在君士坦丁堡所建立起的短暂的拉丁帝国就终结了。拜占庭存活了两个多世纪,期间发生了伟大的文化、艺术和宗教复兴。但是从政治和经济角度来说,重新恢复的拜占庭帝国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发现自己越来越无力应对从东方向其迫近的土耳其军队。
为了获得东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再联合,出现了两次重要的尝试,第一次出现在13世纪,第二次出现在15世纪。第一次尝试背后的推动精神来自光复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迈克尔八世(1259-1282年在位)。虽然他一定会真诚地希望基督教联合建立在宗教基础上,但这次尝试也有政治上的动机:他受到西西里国王——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mjou)的威胁,迫切需要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和保护,获得罗马教廷的支持和保护的最佳方式就是教会联合。
1274年在里昂召开了一次再联合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正教代表同意承认教宗的权柄,也同意使用带有「和子句」的信经。但是这次联合只是纸上协议,因为它遭到了压倒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其中包括拜占庭教会、保加利亚和其他正教国家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对于里昂会议的普遍反应可以概括为"比起正教信仰的纯洁性,我兄弟的帝国更应受到珍视”,人们认为这句话的作者是皇帝的姐妹。迈克尔的继承者正式谴责了里昂的联合会议,迈克尔本人由于"背教”,而被剥夺了基督教葬礼的权利。
与此同时,在对神学和基督教生活的理解方式上,西方和东方的差异更大了。拜占庭继续生活在教父环境中,使用四世纪的希腊教父遗留的思想和语言。而在西欧,教父传统被经院主义(scholasticism)取代了,神学和哲学在12和13世纪进行伟大的综合,形成了经院主义。西方神学家现在开始使用新的观念范畴、新的神学方法、新的专业术语,这些东西无法被东方理解。双方日渐失去共同的"论域"。
拜占庭一方也推动了这个进程:这里的神学发展也没被西方所参与或分享,虽然这里的神学发展不像经院主义革命那样的激烈。这些神学发展主要同「静修士争议」联系在一起,这场争议出现在14世纪中期的拜占庭,涉及上帝本质的教义和正教会的祷告方法问题。
为了理解关于静修士的争议,我们必须回到具有更悠久历史的东方神秘神学。亚历山大的圣克莱门(St.Clement of Alexandria,卒于215年)、亚历山大的奥力振(Origen of Alexandria,卒于253/254年)谋划出神秘神学的主要特征,他们的思想在4世纪的发展者是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特别是尼萨的圣格里高利,还有他们的学生,本都的艾瓦格里乌斯(Evagrius of Pontus ,卒于399年),他是埃及沙漠里的一位修士。这一神秘传统的标志是强烈运用否定方法,运用否定而非肯定的术语来描述天主,这在圣克莱门和圣格里高利那里更是如此。因为人类不能正确地理解上帝,描述祂的一切语言必然都是不确切的。因此否定语言比肯定语言的误导性更小,不说上帝是什么,只说上帝不是什么。就像尼萨的格里高利所说:“关于上帝的真实知识和景象在于认识到祂是不可见的,因为我们所寻找的超出一切知识,被不可理解性的黑暗完全隔离。” 《摩西的生平》
所谓的"狄奥尼修斯的"著作对否定神学做出了古典的表述。数世纪以来,这些著作的作者被认为是亚略巴古的圣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Areopagite),圣保罗宗徒在雅典使他皈依(使徒行实17:34),但是它们其实由一位佚名作者所写,他可能在5世纪末期时居住在叙利亚,也许属于同情非卡尔西顿者的圈子。宣信者圣马克西姆(St.Maximus the Confessor,卒于662年)为狄奥尼修斯的著作写了评论,以此确保它们在正教神学中具有永久的地位。
狄奥尼修斯也在西方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据统计,他在多玛斯亚奎纳的《神学大全》中被引用1760次,据14世纪的一位英国编年史学家记载,狄奥尼修斯的《神秘神学》是"像野鹿一样横穿英格兰"。许多人都重复狄奥尼修斯的否定语言。
大马士革的圣约安说:“上帝是无限的,不可理解的,人对上帝所知的一切就是’上帝是无限的和不可理解的’ ……上帝不属于存在物的等级——不是说祂不存在,二是说祂超越了一切存在物,甚至超越了存在本身。” 《论正教信仰》
上帝的不可理解性是重点,乍看上去似乎要排除任何关于上帝的直接经验。但实际上在那些使用否定方法的人们看来,它不仅仅是一种用哲学的方法,表明上帝是完全超越的,而且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它是一种通过祈祷获得与上帝合一的方式。这些否定表达可以用来限定对上帝的肯定陈述,它还发挥跳板或蹦床的作用,神秘神学家们希望借此从完全的人性跳跃到天主的神秘存在。
例如,尼萨的圣格里高利、狄奥尼修斯和圣马克西姆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倚重于否定方法;对于他们来说,“否定方法"同时也是"合一方法”。但是人们会问,我们怎样能够面对面地遇见那位完全超越的至一呢?上帝怎样能够既是可理解的又是不可理解的?
这是14世纪的静修士面临的问题之一。『静修士』[Hesychast]这个名称来源于希腊词[Hesychia],意思是内在的寂静。静修士献身于静祷之中——只要有可能,这种祈祷剥离一切形象、语言和推论思考的东西。
另一个问题同第一个问题有关联:身体在祈祷中处于什么地位?同奥力振一样,艾瓦格里乌斯有时过于过分地借用柏拉图主义:他使用理智性术语将祈祷表述为心灵的(mind),而非整个人的一项活动,他似乎认为人的身体在救赎和圣化过程中不发挥积极作用。
但是心灵和身体之间的平衡在另一部禁欲主义的作品<玛卡利祷文>(Macarian Homilies)(这些作品的作者传统上被认为是埃及的圣马喀里[St.Macarius of Egypt,?300-390],但是它们现在被认为是4世纪80年代写于叙利亚或小亚细亚的)中得到矫正。<玛卡利祷文>持有更忠于《圣经》关于人的本质教导——人不是囚禁在身体中的灵魂(这是希腊观点),而是一个单独和联合的整体,同时有灵魂和身体。对于艾瓦格里乌斯所讲到的心灵或理智(希腊语为nous),玛卡利使用希伯来文的心(heart)的观念。重点的转变是显著的,因为心指的是整个人——并非仅指理智,而是指意志、感情、甚至身体。
正教徒在玛卡利祷文的意义上使用"心"他们经常谈论"心的祈祷"。这句话的涵义是什么?当某人开始祈祷时,他首先动用嘴唇,他必须努力运用理智进行认识,以了解话语的含义。但是如果那个人在祈祷中持续回忆,理智和心就开始联合:灵找到了"心的居所",获得了"在心中的停留"的能力,所以祈祷成为"心的祈祷"。祈祷不仅是由嘴说出,由心灵思考的东西,而是由人的整体——嘴、理智、感情、意志和身体自发提供的东西。祈祷充满了整个意义,不再是受迫而出,而是自言自语。这种"心的祈祷"不能仅凭我们自己的努力获得,而是上帝的恩宠赐予我们的礼物。
当正教作者们使用"心的祈祷"一语时,他们头脑中常常想着一种特殊的祈祷方式——耶稣祷文。在希腊灵修作家中,首先是弗提塞的迪亚多库斯(Diadochus of Photice,生活在5世纪中期)和后来的西奈山的圣约安.克利马科斯(St.John Climacus of Mount Sinai,?579-?649)不停地重复或回忆"耶稣基督"的名字,将之作为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祈祷形式。
随着时间的发展,圣名祷文开始凝结为一个短句,被称为『耶稣祷文』: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在现代的正教实践中,祷告的结尾有时是,怜悯我罪人(比较税吏的祷告路18:13)
在13世纪以前(如果不是更早),朗诵耶稣祷文已经同一定的身体操练联系起来,用于帮助集中注意力。祈祷时需要仔细调节呼吸,需要身体做出特定的姿势:低头,下巴抵在胸膛上,眼睛注视心脏的位置(*静修士的"方法"和印度瑜伽或穆斯林的迪科尔「Dhikr」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不必深究这些相似之处。)
这常常被称为"静修士的祈祷方法",但是不应该认为这些操练就是修士祈祷的本质。它们不被视为目的本身,而被视为获得专注的帮助手段——只对部分人有辅助性帮助,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静修士们知道不存在获得神恩的机械性方式,以及不存在自动进入神秘状态的技巧。
对于拜占庭的静修士来说,神秘经验的定点是神圣和非受造之光的异象。新神学家圣西蒙(St.Symeon the New Theologian,949-1022)是最伟大的拜占庭神秘主义者,他的话充满了"神秘主义之光"。当他写到自己的经验时,他不断提到神圣之光,他称之为"真正的神圣之火",“非受造、不可见、没有开始、非物质的火”。静修士相信他们经历的这种光就是三位门徒在提波山(Mount Tabor)上看见的变形的耶稣周围的光。但是这个神圣之光异象怎么样同超越和不可接近的上帝的否定神学相调和?
天主的超越性,身体在祈祷中的作用,神圣之光等这些问题在12世纪中期成为首要问题。静修士受到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博学的希腊人,卡拉比的巴拉姆(Barlaam the Calabrian)的攻击,后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论述上帝的"他者性"和不可知性的教义。
人们有时认为,巴拉姆在这里受到当时流传于西方的唯名论哲学的影响,但是他的思想更可能是来源于希腊。他从狄奥尼修斯的片面释经出发,认为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认识上帝,(所以他主张)静修主义错误地讲解对上帝的直接经验,因为在当前生活中,任何这样的经验都是不可能的。
对于静修士使用的身体来操练,巴拉姆指责他们秉持粗陋的物质主义的祷告观念。他也反感静修士声称获得了神圣和非受造之光的异象,在这里他又指责他们陷入了严重的唯物主义之中。人们能怎样用肉眼看到天主的本质呢?在他看来,静修士看见的光不是永恒的神圣之光,而是临时的受造之光。
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ca)大主教,圣格里高利.帕拉玛(St.Gregory Palamas,1296-1359)为静修士做了辩护。他支持的人观允许在祈祷中进行身体的操练,他反驳巴拉姆说,静修士真的经验到提波山上的神圣和非受造之光。为了解释这如何可能,圣格里高利在上帝的本质和上帝的能量之间做出了进一步区分。格里高利为静修主义确立了坚实的教义基础,将之整个纳入到正教神学之中,这是他的成就。
1341年和135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两次会议确立了他的观点,这两次会议虽然只是地方会议而不是大公会议,但在正教神学教义方面却具有不亚于七次全体大公会议的权威。西方基督教世界从未正式承认过这两次会议,虽然西方有许多基督徒个人接受了圣帕拉玛的神学。
圣格里高利帕拉玛一开始就重新确立了关于人和道成肉身的《圣经》中的信理。人是一个单一的联合整体,按照上帝形像创造的不仅有心灵,还有整个人。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灵魂的敌人,而是灵魂的伙伴和合伙人。由于基督在道成肉身时有了人的身体,已经"使身体成为圣化的无穷源泉"。
圣格里高利在这里利用并发展了例如<玛卡利祷文>等早期著作所蕴含的思想。人的身体得到高举,如同我们看到的,关于正教圣像的教义背后强调着身体圣化的教义。圣格里高利继续将以上所提到的人的教义运用到静修士的祈祷方法中,他认为静修士这样强调身体在祈祷中的作用,不会限于物质主义之中,而是忠诚地坚持了《圣经》视人为一个整体的教义。基督具有人的肉体,拯救了整体的人,因此向上帝祈祷的是整个的人——包括身体和灵魂。
圣格里高利从此出发转到了主要的问题:我们人类认识上帝,上帝在本质上是不可能被认识的,如何将这两个命题结合起来。圣格里高利回答说:我们认识的是上帝的能量,而非祂的本质。
上帝的本质(ousia)和能量之间的区别可追溯到卡帕多西亚教父们。圣西里尔说:“我根据上帝的能量认识上帝,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能够接近祂的本质。因为祂的能量降到我们身上,但是祂的本质仍然不可接近。“圣格里高利接受了这种区分。他同否定神学的倡导者一样,强烈断定上帝的本质是绝对不可认识的。他说"上帝不是自然,因为祂超越自然;祂不是存在物,因为祂超越了一切存在物……任何受造物在过去和将来都不能同本质至上者有最细微的交流或接近。“但无论祂的本质距离我们有多遥远,上帝却在其能量中向我们显示祂自己。这些能量不是独立于上帝而存在,不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它们是活动中的上帝本身和面向世界的启示。上帝在其全部神圣能量中完整而完全地存在。
正如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所说,世界充满了伟大的上帝,所有受造物都是巨大的燃烧灌木,奇妙而壮丽的上帝的能量之火散布于其中,而不是将其烧毁。
通过这些能量,上帝与人有了直接而立即的关系。在同我们人类的关系中,上帝的能量实际上只是上帝的恩典;恩典不仅仅是上帝的"礼物”,不仅仅是上帝赐予人的客体,而是活生生的上帝本身的直接展现,是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亲自相遇。
“只要恩宠与人相交,它就代表天主性的完整和丰足。”——《东部教会的神秘神学》(The Mystical of the Eastern Church)
当我们说圣人已经被上帝的恩宠改观或"圣化”,我们的意思是他们对上帝本身有了直接的经验。他们认识上帝——也就是说,认识上帝的能量,而不是上帝的本质。
上帝是光,因此对上帝之能量的经验采取了光的形式。(圣格里高利帕拉玛认为)静修士接受的异象不是受造之光的象,而是神圣之光的异象,同提波山上围绕着基督的神光一样。这光不是可感知的或者物质之光,但是能够被肉眼所看见(就像门徒们在基督显圣容时看到的那样),因为当一个人圣化时,他的身体机能和灵魂一起变形。静修士看到的光是真实的上帝的能量,把它和提波山上的非受造之光相等同,这是相当正确的。
于是,帕拉玛维护了上帝的超越性,避免了不审慎的神秘主义容易导致的泛神论;尽管他的观点允许上帝具有内在性,因为上帝持续存在于世界之中。上帝仍然是"全然的他者”,祂通过祂的能量(即上帝本身),进入到与世界的直接关联中。上帝是活生生的上帝,历史之上帝,《圣经》之上帝,祂道成肉身为基督。
巴拉姆摒除关于天主的一切直接知识,断言神圣之光是受造的,在天主和人之间设置一条宽广的鸿沟。圣格里高利帕拉玛反对巴拉姆,是基于和圣阿塔纳修斯以及全体大公会议同样的考虑:保卫我们通向上帝的直接进路,支持我们完全的圣化和救赎。支垫起神圣三位一体、基督位格、圣像争论的同一个关于救恩的信理,也就是静修士争论的中心。
迪克斯(Dom Gregory Dix)写道:“在6世纪以前,封闭的拜占庭世界内没有真正的新鲜推动力……。在9世纪,甚或更早在6世纪……沉睡开始了。"《礼仪的形成》拜占庭在14世纪的争议充分证明了上述论断是错误的。圣格里高利帕拉玛无疑不是革命性的创新者,但他坚实地根植于过去的传统之中,他是第一流的有创造力的神学家,他的作品显示出正教神学没有在8世纪和第7次大公会议以后丧失活力。
在帕拉玛的同时代人中,有一位平信徒神学家圣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St.Nicolas Cabasilas)是静修士的同情者,尽管他没有深深卷入到这场争论中。卡巴西拉斯写了《神圣礼仪评论》(Commentary on the Divine Liturgy),该书已经成为正教会关于这一主题的经典之作;他还写了一步关于圣事的著作,名为《基督中的生命》(The Life in Christ)。
卡巴西拉斯的著作有两个极为明显的特征:对于拯救者基督之位格有生动的感知,他说基督"比我们自己的灵魂同我们更接近”;他反复强调圣事。对于他来说,神秘生活在本质上是基督之生活和圣事之生活。神秘主义具有冥想性和个人主义的危险——同基督的历史启示和教会的圣事共同生活相分离,但是卡巴西拉斯的神秘主义始终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圣事的、教会的。他的著作显示了神秘主义和圣事生活在拜占庭神学中紧密联系。圣格里高利帕拉玛及其圈子没有把神秘的祈祷视为避开正常的教会制度性生活的一种方式。
第二次再联合会议于1438至1439年在佛罗伦萨召开。出席者有皇帝约翰八世(1425-1448年在位)本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拜占庭教会的庞大代表团,还有其他正教会的代表。讨论被延长了,双方为了就重要的争论问题达成真正的一致意见。与此同时,希腊人难以冷静地讨论神学,因为他们发现政治形势现在变得危急:打败土耳其人的唯一希望寄托在西方的帮助上。最终,一个包含「和子句」、炼狱论、无酵饼和教宗权的联合方案被制定出来,除了艾弗所大主教,后来被正教会封为圣人的圣马尔克(St.Mark)以外,所有与会的正教徒都在方案上签了字。
佛罗伦萨联盟建立在一个双重原则上:在教义事务上一致;尊重各教会专属的合法礼仪和传统。因此在教义的问题上,正教接受了教宗权(虽然联合方案的措辞在某些方面是模糊含混的);他们接受了圣灵的双重生和发的教义,虽然他们不需要在礼仪中使用的信经文本上加入「和子句」;他们接受了罗马关于炼狱的教义(作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个争议问题,在13世纪走向公开)。但是就无酵饼的问题来说,不需要达成一致:允许希腊人使用发酵饼,而拉丁人继续使用未发酵饼。
但是虽然整个西欧都为达成佛罗伦萨联盟而庆祝——英格兰的所有教会教区都鸣钟——结果它在东方不比先前的里昂协定更现实。约翰八世和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十一世都忠诚于协定,后者是拜占庭的末代皇帝,是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的第80代皇帝;但是他们无力在臣民中推行它,甚至在1452年以前不敢在君士坦丁堡公开宣布它。许多在佛罗伦萨签字的人回家后都撤销了他们的签名。绝大部分拜占庭的神职人员和民众从未接受会议决定。
卢卡斯?诺特拉斯(Lucas Notaras)大公爵模仿了皇帝的姐妹在里昂协定以后说的话,他说:“我宁愿在城中看见包头巾的穆斯林,也不愿看见戴主教冠的拉丁人。”
约翰八世和君士坦丁十一世曾经希望佛罗伦萨联盟会帮助他们得到西方的军事援助,但是他们实际得到的帮助却微乎其微。
在1453年4月7日,土耳其人开始从陆路和海路攻击君士坦丁堡。在超过20比1的人力对比情况下,拜占庭人开展了光荣而无望的抵抗,持续了7个星期。在5月29日的较早时分,最后一场正教的事奉圣礼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它是正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的联合礼拜,因为佛罗伦萨联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这一危急时刻都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皇帝在领受了圣体血后就出去了,死在城墙上的战斗中。
土耳其人后来在那天攻入城中,基督教世界中的大多数雄伟的教堂变成了清真寺。
拜占庭帝国结束了。但是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没有结束,正教更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