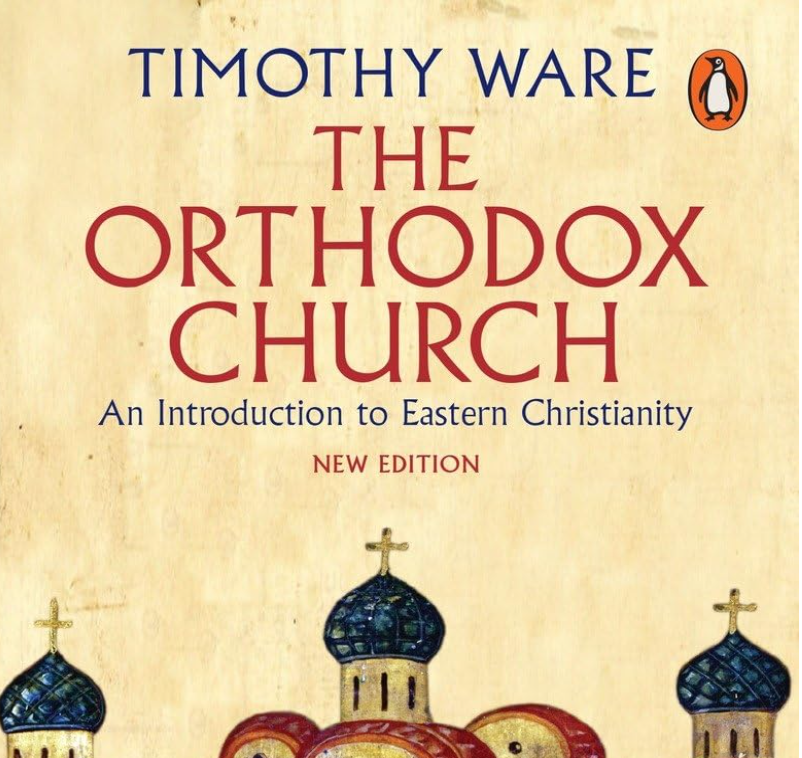-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课系列第九课,黑暗时代——伊斯兰下的东正教。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九课:伊斯兰下的东正教》,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11月22日),讲稿由阿甲整理而成,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 本讲稿由阿甲修订,很多内容参考这个中译本。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论》,中译田原(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若无特别说明,文字均是维尔主教的中译。若有阿甲的按语,则会写上:“阿甲按”三个字,并以引用符号标出。
油管订阅,下载音频和视频,请见这里
正文 第五章 伊斯兰下的东正教
第五章 伊斯蘭教徒統治下的教會
阿甲按:伊斯兰教下的教会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通过将基督教变成二等宗教,基督徒变成二等公民,繁重的赋税,买卖总主教,禁止传教,限制出版物等全方位的手段,将基督教变成一个少数群体,最终凡是伊斯兰下的基督教都可以说是黑暗时期,只能力图自保而已。并且还不时爆发专门针对基督徒的屠杀活动。可以说,伊斯兰对基督教的压制超过所有世俗政权对基督徒迫害和压制,因为后者的迫害和压制是有时间限制的,是时断时续的,但伊斯兰下的基督教是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压迫,这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希臘教會在我們的時代堅定不屈 ……儘管它受到土耳其人壓迫和蔑視,這個世界上的誘惑和快樂,同世界初始時就有的奇蹟和大能,有着同樣的説服力和確定性。了解和思考無知而貧窮的人們多麼堅定不移、勇敢果斷、簡單率直地保持他們的信仰,真的非常令人欽佩。
—菜科特爵士(Paul Rycaut)
《希臘和亞美尼亞教會現狀》(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Greek and Armenian Churches, 1679)
一、帝國內的帝國
「在十字架曾勝利地樹立了那麼久的地方看到新月到處升起,實在大背常理」,布朗尼(Edward Browne)在一六七七年這樣説,其時正值他以神父身份到達君士坦丁堡的英國大使館之後不久。對於希臘人來説,一四五三年必定也大背常理。因為在一千多年的時間裏,人們把拜占庭的基督教帝國當作上帝對世界天佑神意的一個永久性要素。現在,「受上帝保護的城市」已經論陷,希臘人處於異教徒的統治之下了。
這個轉變不容易,但是土耳其人使它的艱難少了一些,他們在對待他們的基督徒臣民時相當寬厚。十五世紀的穆斯林對待基督教遠比西方基督徒在宗教改革和十七世紀時的彼此互待更加寬容。伊斯蘭教認為《聖經》是一部聖書,耶穌基督是一位先知,所以在穆斯林的眼中,基督宗教在某些問題上有錯誤,但不是全然荒谬,基督徒是「聖書之民」,不應該僅在異教徒的層面上對待他們。按照穆斯林的教義,基督徒不應該遭受迫害,只要他們安靜地服從伊斯蘭教的權力,他們的信仰就不受干涉地繼續下去。
這些原則指引着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蘇丹默罕默德二世Mohammed II)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前,希臘人稱他為「反基督的先驅和第二位西拿基立(Sennacherib) 」(亞述國王、公元前七0五至六八一年在位,曾兩度侵犯猶大國,亦曾擊敗巴比伦。) ,"但是他們發現他的統治其實具有非常不同的特微。當默罕默德得知宗主教職位空缺時,他召來修士根那迪烏斯(Gennadius) ,讓他就任宗主教職位。根那迪烏斯(?1405—?1472)在當修士以前就以喬治·斯科拉里奥斯(George Scholarios)的名字聞名,是著述等身的作家和當時最重要的希臘神學家。他堅決反對羅馬教會,任命他為宗主教意味着佛羅倫薩聯合協定最終被拋棄。蘇丹故意選中一位具有反拉丁信念的人擔任宗主教,這無疑具有政治原因:根那迪烏斯成為宗主教,希臘人尋求獲得羅馬天主教力量秘密支持的可能性就減小了。
蘇丹親自委任宗主教,動用禮儀授予他教牧職位,恰如拜占庭獨裁者們以前的作為。這一舉動具有象徵性:征服者、伊斯蘭教的戰士默罕默德,也成為正教的保護者,接手了一度曾由基督徒皇帝施行的任務。因此基督徒在土耳其社會秩序內的確定地位得到保證,但是正如他們不久後發現的,這種地位必定是低級地位。伊斯蘭教徒統治下的基督教是二等宗教,它的擁護者是二等公民。他們繳納重税,穿着特殊服飾,不允許服役,禁止同穆斯林女子結婚。教會的傳教工作不被允許,使穆斯林轉信基督教信仰是犯罪。從物質的觀點來看,基督徒背教成為穆斯林的誘惑無處不在。直接的追害常常增強教會的力量,但是奥斯曼帝國的希臘人通常被剝奪了更加英勇地見證他們信仰的方式,相反卻要承受無情的社會壓力帶來的沮喪結果。
情况不止於此。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後,教會不得恢復君士坦丁皈依以前的狀態,這頗具悖論性,「歸凱撒的」現在較以前任何時候都同「歸上帝的」有更緊密的聯繫。因為穆斯林沒有在宗教和政治之間做出區分:在他們看來,如果基督教被視為一個獨立的宗教信仰,基督徒必須被組織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單位,一個帝國中的帝國。正教會因此既是世俗的也是宗教的機構:它變成「羅馬國家」(Rum Mille)。教會組織完全變成世俗管理的工具。主教變成政府官員,宗主教不但是希臘正教會的靈性首領,還是希臘國家的世俗首領——統治者(ethnarch)或政治首领(miller—bashi) 。這—情況在土耳其延續到一九二三年,在塞浦路斯延續到大主教馬卡里阿斯(Makarios)三世去世時(1977年) 。
這一政治(millet)體制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使得作為一個特殊單位的希臘國家有可能在外來統治下維持四個世紀。但是它給教會生活帶來兩個悲慘的結果。首先,它導致正教和民族主義悲哀地混淆在一起。希臘人的世俗生活和政治生活完全圍繞教會組織起來,他們幾乎不可能區分出教會和國家。普世的正教信仰不限於單個的人、文化或語言,但是對於土耳其帝國內的希臘人來説,「希臘文化」和正教不可避免地糾結在一起,其程度遠遠超過拜占庭帝國內的任何時期。這種混淆的結果一直延續到今天。
第二,教會的高級管理開始陷入腐敗和買賣聖職的可恥體系中。當主教們捲入世俗事務和政治事務時,他們堕落為野心和財務贪婪的犧牲品。每位新宗主教在就任前都需要獲得蘇丹的授權書,他不得不花重金獲取這份文件。宗主教的花費在他的主教轄區得到補償,他在教區勒索所有被委任聖職以前的主教們,主教們接下來勒索教區的神父,神父勒索他們的信徒。一切都是有償出售的:曾經適用於羅馬教廷的指責肯定也適用於土耳其人統治下的普世宗主教區。
當幾位候選人競爭宗主教職位時,土耳其人實際上把它賣給出價最高的人,他們很快注意到儘可能頻繁地更宗主教,以此增加售賣授權書的機會符合他們的財政利益。宗主教被撤職和復職的速度令人眼花繚亂。「在十五到二十世紀間的一百五十九位就職的宗主教中,土耳其人一百零五次將宗主教趕下台;退位有二十七次,常常是自願的;六位宗主教由於绞刑·毒藥或溺水而慘死;只有二十一位宗主教在位時自然死亡。」1同一個人有時上台四五次。時常還有幾位前宗主教在流放期間虎視眈眈地伺機重新掌權。宗主教極具不安全感,自然導致連绵不斷的陰謀出現在有望接替他的神聖會議都主教中,教會的领袖們常常分裂成殘酷敵對的派系。
七世紀居住在列凡特(Levant)的一個英國人寫道:「每個良善的基督徒都應該帶着悲傷去思考,帶着同情去目睹這個曾经辉煌的教會撕破她自己的腸腑,讓禿鷹和烏鴉,世界上野蛮而殘忍的動物吃掉它們。21B.kidd《东部基督教世界的教会)( The Churches of EasTern christendom 1927),页304
2.Sir PauI Rycaut《希腊和亞美尼教会的现状)
但是如果說君坦丁堡宗主教區遭受内部的衰敗,它的勢力則在外部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展。土耳其人把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視為其疆域内所有正教基督徒的領導者。其他宗主教區如亞歷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也都位於奧斯曼帝國,它們從理論上說是獨立的,但實際上處於從屬地位。同様受土耳其人控制的保加利亞教會和塞爾維亞教會,逐漸喪失了完全的獨立,到十八世紀中期時直接受普世宗主教控制。但是在十九世紀,隨着土耳其勢力的衰微,宗主教區的邊界收縮了。擺脱土耳其人控制的國家發現,繼續在教會事務上臣服於一個在土耳其首都居住並深深卷入土耳其政治體制的宗主教是不切實際的。宗主教千方百計地對之抵制,但每次最终都在必然性面前無可奈何。一系列民族教會脱離了宗主教區:希臘教會(一八三三年組建,一八五0年得到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認可) ;羅馬尼亞教會(一八六四年組建,一八八五年被承認) ;保加利亞教會(一八七一年重建,直到一九四五年才被承認) ;塞爾維亞教會(一八七九年恢復和被承認) 。宗主教區的縮小持續到二十世紀,這主要是由於戰爭,它在巴爾幹半島的成員數現在只是它在奥斯曼帝國政權興盛時期的一小部分。
土耳其人的占领給教會的知識生活帶來兩個相反的結果:它一方面是巨大的保守主義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一定程度的西化的原因。土耳其人統治下的正教發現自身處於守勢。最大的目標就是生存——在對更佳時日來臨的期待中維持事務運行。希臘人具有奇蹟般的韧性,堅持他們從拜占庭那裏承襲而來的基督教文明,但是幾乎沒有機會創造性地發展這一文明。他們常常滿足於重複已被確認的公式,對自己過去所繼承的立場墨守成規,這很好理解。希臘思想陷入僵化和硬化之中,這不得不令人遺憾,然而保守主義也有其自身優勢。希臘人確實在一個黑暗而艱難的時期,使正教傳統大體上未受損傷。受伊斯蘭教徒統治的正教徒以保羅講給提摩太的話為指引: 「你要保守所託付你的。」(提前6:20)他們最後選中更好的箴言了么?
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正教神學中,與保守主義相並行的還有另外一個相反的潮流:西方的滲透大潮。對於奥斯曼帝國統治下的正教徒來説,維持優秀的學術水準是困難的。想要獲得高級教育的希臘人不得不前往非正教世界,去意大利和德國,去巴黎,甚至是牛津。在土耳其時代的傑出希臘神學家之中,有少數人是自學的,但是絕大多數人在西方接受羅馬天主教或新教教師的培養。
這必然對他們解讀正教神學的方式產生影響。希臘學生必然會在西方閲讀教父們的著作,但是他們只熟悉他們的非正教徒教授們所尊敬的教父的著作。所以雖然阿索斯的修士們仍然閱讀格列高利·帕拉瑪的靈修著作,但是對於土耳其時代大多數博學的希臘神學家來説,他完全不為人知。優斯特拉提奧斯·阿根迪(Eustratios Argenti 卒於?1758年)是其時代中最有能力的希臘神學家,他的著作一次也沒有引用帕拉瑪,是個典型的例子。帕拉瑪的一部主要作品《保衛神聖靜修士的三段編》( The Triads in Defence of the Holy Hesychasts)直到一九五九年時還有大部分未被出版,這表現出希臘正教神學在過去四個世紀中的狀況。
雖然在西方學習的希臘人在意圖上完全忠實於他們自己的教會,但是也有喪失其正教精神同作為一個活生生傳統的正教相割裂的真正危險。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他們看待神學時很難不借助西方視角,他們使用同他們自己教會相異的術語和論辯形式。用俄羅斯神學家弗洛羅夫斯基(Georges Florovsky,1893-1979)的恰切術語來説,正教神學經歷了偽的構形( pseudomorphosis)。土耳其時代的大部分宗教思想家能被劃分為兩大類:「拉丁化的人」和「新教化的人」。然而,西化的程度不應被誇大。希臘人使用他們在西方學得的外在形式,但是他們的思想實質大部分基本上還是正教的。這一傳統不時地被陌生模型的力量所歪曲只是被歪曲,而不是被全然摧毁。
將保守主義和西化的雙重背景謹記於心,讓我們思考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給正教世界帶來的挑戰。
二、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雙重影響
宗教改革力量到達俄羅斯和土耳其帝國的邊界時突然停止下來,所以正教會既沒有經歷宗教改革,也沒有經歷反宗教改革。可是如果得出結論説這兩個運動沒對正教產生影響,卻是錯誤的。存在着多種接觸方式: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正教徒在西方學習;耶穌會會士和方濟各會修士被派到地中海地區東部,在正教徒中開展傳教工作;耶穌會士也在烏克蘭工作;羅馬天主教和新教在君士坦丁堡的外國使館發揮了宗教和政治作用。在十七世紀期間,這些接觸推動正教神學取得重要進展。
正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第一次重要的意見交換始於一五七三年,由雅各布·安德雷(JakobAndreae)和馬丁·克魯修斯( Martin Crusius)帶領的路德宗學者代表團從圖賓根(Tubingen)出發,訪問君士坦丁堡,攜帶一份譯成希臘文的(奧斯堡信綱(Augsburg Confession),將之交給宗主教耶利米二世(Jeremias II)毫無疑問,他們希望在希臘人中發起某種宗教改革,如同克魯修斯有些幼稚的記錄所説:「如果他們想要考慮他們的靈魂永得救贖,他們必須加入我們,信奉我們的教義,否則就永遠毀滅!」可是,耶利米在他寫給圖賓根神學家的三封《回信》(Answers)(日期為1576,1579、1581年)中,嚴格堅持傳統的正教立場,沒有顯示出對新教有偏向。路德宗徒回覆了前兩封信,但是宗主教在第三封信中结束了對話,感覺到事情陷入了僵局:「走你自己的路吧,不要再寫信討論教義問題了;如果你寫信,那麼只為友谊而寫吧。整個事件示出正教會的改革家們的興趣從正教的點来看,作為宗教改革教義的第一次清晰和权威的批判,宗主教的回應具有重要意義。耶利米讨論的主要問题是自由意志和恩典·《圣經》與傅統,圣事,為死者祷告和圣徒的祈禱間题。
在图宾根插曲期間,路德宗徒和正教徒都對對方極其殷勤。正教和反宗教改革力量之間的第一次主要接觸,以一個極其相異的精神為標誌。它發生在土耳其帝國的疆域之外,發生在乌克蘭。在鞑靼人摧毁了基辅的力量以後,包括基辅城在内的俄羅斯西南部大片區域被立陶宛人和波蘭人吞併,俄羅斯的西南部分通常被稱為「小俄羅斯」或鳥克蘭。自從一三八六年起,波蘭和立陶宛的王權歸一人所有而實現統一,可是這個聯合王國的君主和絕大多數臣民是羅馬天主教徒,少數臣民是俄羅斯人和正教徒。烏克蘭的正教徒處於不幸的困境中。他們受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管理,可是宗主教在波蘭没有非常有效的控制力,他們的主教不是由教會任命,而是由波蘭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國王任命,有時由缺乏靈性特質的朝臣任命。
在十六世紀快要結束時,朝向羅馬的運動在烏克蘭东部的基督徒中得到發展。在一五九六年的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會議上,與會的八位主教中有六位決定支持與羅馬聯合,這六位主教包括基輔的都主教拉古薩(Michael Ragoza),而其餘兩位主教,還有很多修道院代表和教區代表選保留正教。尖锐的分裂出现了:一方要繼續當正教徒,另一方要成為「希臘天主教徒」、「東儀天主教徒」·「東方合一教徒」,這些都是他們的不同名稱。希臘天主教徒接受佛羅倫薩會議的原則:他們承認教宗至高無上,但是被允許保持他們傅統的實踐,例如允許神父結婚,他們繼續像以往一樣使用拜占庭禮儀,儘管西方的元素隨着時間發展慢慢滲入其中。所以從外在表現上説,東儀天主教徒和正教徒幾乎沒有區別。人們會產生疑問,沒有接受教育的農民能夠明白這場爭論究竟是關於甚麼嗎?
在波蘭的鳥克蘭繼續作正教徒的人受到羅馬天主教當權者的嚴重壓制,毫無疑問,布雷斯特聯盟使正教和羅馬的關係自一五九六年開始變得苦涩,一直持續到現在。然而,迫害以多種方式起到了激勵作用。平信徒團結起來保衛正教,許多地方的高級神職人員投靠羅馬,被稱為兄弟會(Bratstva)的強有力的平信徒聯合會,在那些地方維護正教傳統。為了應對耶穌會士的宣傳活動,他們開辦印刷廠,發放保衛正教的書籍;為了回擊耶穌會學校的影響力,他們組建了自己的正教學校。到一六五0年時,烏克蘭的學問水平比正教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高,來自基輔的學者們在這時前往莫斯科,為了提高大俄羅斯的知識水平而出力甚多。在這場知識復興中,一六三三年至一六四七年在位的基輔都主教莫吉拉的彼得(Peter of Moghila)發揮的作用尤為出色。稍後我們必須再次説論他。
一位名叫西里爾·鲁卡里斯(Cyil Lukaris, 1572—1638)的年輕希臘神父,是出席一五九六年布雷斯特會議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區的代表之一。不論是由於他在鳥克蘭的經歷,還是由於他隨後在君士坦丁堡結下的友誼,他後來對羅馬教會具有強烈的敵意。一成為普世宗主教,他就將全部精力用於同土耳其帝國內的羅馬天主教勢力抗爭。不幸的是,在他同「帕皮奇教會」(Papic Church) (希臘人這樣稱呼它)鬥爭的時候,據説他深深地涉入到政治當中,但這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他自然向君士坦丁堡的新教使館尋求幫助,而他的耶穌會對手則動用了羅馬天主教勢力的外交代表。除了尋求新教外交官的政治幫助,西里爾的神學觀念也受到新教的影響,他的《信仰告白》(Confession)3於一六二九年在日内瓦首次出版,其中的許多教義都具有鮮明的加爾文主義特徵。
3.此處使用的"Confession"一詞表示信仰的陳述宗教信仰的莊嚴宣示
在西里爾的宗主教職任期,潛伏着一連串狂暴的陰謀,形成了一個恐怖的例子,顯現出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普世宗主教區的混亂狀況。他被免職六次,被復職六次,最終被土耳其士兵絞死,屍體被拋到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中。他的一生最終是一個巨大的悲劇,因為他可能是聖弗提烏斯以後最卓越的宗主教。如果他生活在更為順暢的環境中,不經歷政治陰謀,他的優異天資或許能得到更好的運用。在西里爾的加爾文主義迅速遭到他的正教徒同夥的尖刻批判,他的《信仰告白》至少在一六三八年到一六九一年間受到六次地方會議的譴責。在直接應對西里爾的過程中,其他兩位正教大主教,莫吉拉(Moghila)的彼得和耶路撒冷的多西修斯(Dositheus)寫了他們自己的信仰告白。彼得的《正教信仰告白》(Orthodox Confession)寫於一六四0年,直接以羅馬天主教手冊為基礎。一位叫麥勒修斯·塞里格斯(Meletius Syrigos)的希臘人特别修訂了其中關於聖餐祝聖(聖事禮儀言語[Words of Institution完全功歸於彼得)和煉獄的段落,它之後在羅馬尼亞的亞西(Jassy)會議(1642年)上獲得通過。即使莫吉拉的信仰告白在被修訂以後,它仍然是正教會的正式會議所接受過的最具拉丁化的文件。多西修斯在一六六九年到一七0七年間當選為耶路撒冷宗主教,他同樣大力汲取拉丁資源。他的《信仰告白》在一六七二年獲得了耶路撒冷會議(也被稱為伯利恒會議)的正式批准,簡明而清晰地逐點回應了西里爾的《信仰告白》。
西里爾和多西修斯主要在四個問題上有分歧:自由意志,恩典,預定的問題;教會教義;禮儀的數目和性質;聖像崇拜。
多西修斯論述聖餐時,不但採納了拉丁術語變質(transubstantiation),還採納了經院主義對於本質(substance)和偶性(accidents)的區分;他的為死者禱告的教義同羅馬的煉獄教義非常接近,但沒有真正使用煉獄一詞。從整體上説,多西修斯的《信仰告白》的拉丁化程度要遜於莫吉拉的《信仰告白》,必定能被視為十七世紀正教神學歷史上具有頭等重要性的文獻。面對魯卡里斯的加爾文主義,多西修斯使用了手邊最近的武器——拉丁武器(在這樣的背景下,這或許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但是他使用這些拉丁武器保衛的信仰卻不是羅馬的,而是正教的。
在烏克蘭以外的地區,正教和羅馬天主教在十七世紀的關係常常是友好的。在地中海地區東部的許多地方,特別是在威尼斯人統治下的希臘群島上,希臘人和拉丁人互相分享對方的禮儀:我們甚至讀到大批穿着全套法衣,帶着蠟燭和旗幟的正教神職人員加入羅馬天主教的聖餐禮遊行。希臘主教們邀請拉丁傳教士向他們的信眾宣道或者聆聽告解。但是在一七00年以後,這些友好的接觸不如以前頻繁了,到一七五0年時基本停止。正教的安提阿宗主教區的很大部分在一七二四年服從於羅馬,此後的正教當權者害怕同樣的事情在土耳其帝國的其他地方再度出現,於是在同羅馬天主教的關係上變得極為嚴厲。反羅馬情緒的高潮在一七五五年出現,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和耶路撒冷的宗主教宣佈拉丁洗禮完全不合法,要求所有皈依正教的人重新洗禮。「必須抛棄和憎惡異教徒的洗禮」,這項命令宣稱,它們是「沒有益處的水……也不能使那些接受它的人們聖化,對滌清罪惡沒有一點幫助」。直到十九世紀末期時,這項政策仍然在希臘人中有效,但是沒有被俄羅斯教會採納,俄羅斯人通常是在一四四一年到一六六七年間為羅馬天主教皈依者洗禮,但是自從一六六七年以後就沒有這樣的正式行動了。
十七世紀的正教不但開始接觸羅馬天主教徒路德宗徒和加爾文宗徒,還接觸了英國教會。西里爾·魯卡里斯聯絡了坎特伯雷大主教修道院長和未來的亞歷山大宗主教梅特羅法尼斯·克里托普勒斯(Metrophanes Kritopoulos),後者一六一七年至一六二四年在牛津學習。克里托普勒斯是《信綱》( Confession)的作者,這部《信綱》具有些許新教調子,但是被正教會廣泛使用。牛津的格洛斯特堂(Gloucester Hall)(现在的伍斯特Worcester学院)甚至在一六九四年左右有了創辦「希臘學院」的計劃,確實有十名左右的希臘學生被送到牛津,但是由於資金的缺乏,這個計劃破產了,希臘人發現食宿很低劣,所以許多人都逃走了。在一七一六年到一七二五年期間,正教和非誓從者(Non-jurors)(在一六八八年脱離英國教會主體的一群聖公會教徒,而不是發誓效忠篡位者奧蘭治的威廉[usurper William of Orange]的那群人)之間一直保持的通信非常有意思。非誓從者們懷着與正教徒建立共融的希望,接洽了四位東方宗主教和俄羅斯教會。但是非誓從者不能接受正教的基督臨現於聖餐的教義,正教對聖母、聖徒和聖像的敬奉也困擾了他們。最終,通信中止了,沒有達成任何一致意見。
回顾莫吉拉和多西修斯的工作,亞西和耶路撒冷會議,同非誓從者的通信,觸動人們的是希臘神學在這一時期具有的局限性:人們找不到完满的正教傳統。但是十七世紀的宗教會議對於正教有着永久而富有建設性的貢獻。宗教改革爭論提出的問題不是大公會議和後來的拜占庭帝國教會要面對的問题:正教在十七世紀不得不更多地思考聖事,教會的性質和權威等問題。正教的要務是阐釋它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明確自己對於西方出現的新教義的立場,這是十七世紀的會議實現的任務。這些會議是地方性的,但是會議決定的精神已被正教會通盤接受。同三百年前的靜修士會議一樣,十七世紀的會議顯示出正教會的創造性神學工作在大公會議時期以後沒有終結。每位正教徒都要把大公會議的決定視為其信仰的組成部分去接受,但是許多重要的教義沒有被大公會議確定。
Philokalia 《爱神集》
在土耳其人統治時期,靜修主義傳統自始至終都保持着活力,特別是在阿索斯山上。一個重要的靈性復興運動在十八世紀後半期出現,我們現在仍能感受到它的影響。其成員被稱為煮麥派(Kollyvades) ,太多的希臘同伴在西方啟蒙運動的影響下走上歧途,這使他們感到不安。煮麥派相信希臘民族的復興將要來臨,這不是通過採納西方流行的世俗觀念,而只能通過重返正教基督教的真正根源——通過重新發現教父神學和正教的禮儀生活而實現。他們特別倡導頻繁地領受聖餐——如果可能,每天領受——雖然大多數正教徒在當時每年只領受三或四次。由於這一點,聖山和別處的煮麥派都受到強烈攻擊,但是一八一九年在君士坦丁堡召開的一次會議接受了他們的立場,確認信眾如果準備恰當,原則上可以在每次舉行聖餐禮時接受聖事。
這場靈性復興的最突出成就是《慕善集》 (Philokalia)的出現,它是一本大部頭選集,收錄了從四世紀到十五世紀的禁欲主義和神秘主義著作。這本厚重的書一七八二年在威尼斯出版,大約有一千二百零七個對開頁。編者既包括煮麥派運動的領軍人物,哥林多都主教聖馬喀里(諾特拉期[Notaras, 1731—1805] ) ,還包括聖山的聖尼哥底母(Nicodemus the Hagiorite, 1748-1809),他被公正地冠為「當時的阿索斯山學問百科全書」。《慕善集》的編者想讓世界上的平信徒和修士都成為此書的受眾,此書特別用於內在禱告,特別是耶穌禱吿的理論和實踐。它在希臘世界中的影響最初有限,過了一個世紀才重新發行。但是斯拉夫譯本於一七九三年在莫斯科出版,這對十九世紀的俄羅斯靈修復興做出了决定性貢獻。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的晚近時期,希臘人對《慕善集》給予了更多的關注。西方語言的譯本也開始出現了,這些譯本吸引了為數令人驚奇的讀者。《慕善集》其實起到了靈修「定時炸彈」的作用,因為真正的「《慕善集》時代」不是十八世紀晚期,而是二十世紀晚期。
尼哥底母幫助修訂了其他許多著作,最著名的是新神學家西蒙的著作,他準備了一部格列高利·帕拉瑪的選集,雖然從未出版。多少有點令人奇怪的是,鑒於當時希臘世界中強烈的反天主教情感,他也吸收了羅馬天主教的虔敬文獻,使洛倫佐·斯卡波利( Lorenzo Scupoli)和耶穌會的創建者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Loyola)的著作適合希臘的正教讀者。
在十八世紀,阿索斯山的另一位修士艾托里亞的聖科斯瑪(St Kosmas the Aetolian,1714-1779)不是通過書本,而是通過傳教宣講促進了希臘人的復興。他的傳教使人想起約翰·衛斯理(JohnWesIey)。在土耳其人統治下,當希臘人的宗教和文化生活在許多地方陷入極低的低潮時,他的一系列使徒式旅行遍及希臘大陸和島嶼,他向大批群眾宣道。他認為希臘正教和希臘語言是互相聯繫的整體,他在所到之處創辦希臘學校。最終,他被奧斯曼帝國當權者處死。他是土耳其帝國時代許多為信仰而受難的「新殉道者」之一。
土耳其時代的正教有多少值得惋惜之處,就有多少值得欽佩之處,這句話是正確的。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正教會儘管有無數的挫折,但從未喪失精神。當然有許多人背教後皈依了伊斯蘭教,但是無論如何,歐洲的背教情況不如預期的那樣頻繁。雖然教會高級管理中存在的腐敗令人沮喪,但它對普通基督徒日常生活的影響微乎其微,他們在每個主日仍然會去自己的教區教會進行禮拜活動。在那些黑暗的日子中,最能保持正教活力的是神聖禮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