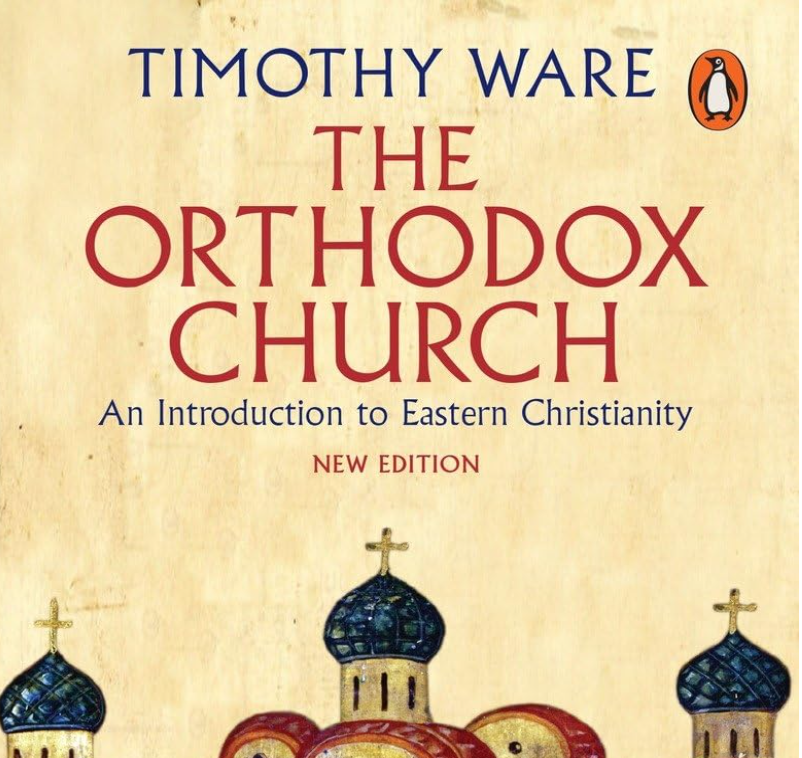-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13课 20世纪散居的东正教。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12课:20世纪的东正教与无神论》,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5年01月24日),讲稿由阿甲整理而成,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斯斯
- 本讲稿由阿甲修订,很多内容参考这个中译本。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论》,中译田原(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若无特别说明,文字均是维尔主教的中译。若有阿甲的按语,则会写上:“阿甲按”三个字,并以引用符号标出。
油管订阅,下载音频和视频,请见这里
正文 第9章 20世纪的东正教与无神论
第九章 二十世紀之三:流徙和使命
所有異鄉都是我們的祖國,所有祖國都是異鄉。——《丢格那妥書信》5:5
一、合一的多樣性
從文化和地理的觀點而言,過去的正教幾乎只是作為一個「東方的」教會出現·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様。正教徒廣泛「散佈」於傳統的正教國家疆域以外,其主要中心是北美,但是世界的每個部分都有分支。論人數和影響力,希臘人和俄羅斯人佔據主導地位,但是流徙絕不僅僅限於他們,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及其他人都擁有一席之地。
正教徒的流徙始於很早以前。倫敦的第一個希臘教會早在一六七七年開放,位於當時時髦的蘇荷(SOHO)區。它的生涯短暫而不順利,在一六八二年被關閉。倫敦的聖公會主教康普頓(Henry Compton)禁止希臘人在教堂中擁有聖像,要求他們的神職人員略掉所有聖徒禱告,不承認耶路撒冷會議(1672年),拒絕「變質説」教義。當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向英國大使芬奇(John Finch)爵士抗議這些情況時,後者反駁,「在英國的公共教堂表達羅馬的信仰是不合法的,表達希臘信仰同表達羅馬信仰一樣不合法。」1
在倫敦建立的第二個正教崇拜地點是俄羅斯大使館教堂,它在一七二一年左右開放,享有外交豁免權,所以英國的聖公會主教不會注意裏面發生甚麼。在十八世紀使用這個教堂的是希臘人丶英國皈依者和俄羅斯人。希臘人於一八三八年能夠在倫敦開辦一所他們自己的教堂,聖公會領導者沒有做出任何刁難限制。
正教自十八世紀中期以來出現在北美大陸·俄羅斯探險家白令(Bering)和奇里科夫(Chirikov)於一七四一年七月十五日發現阿拉斯加海岸,在五天後的先知伊利亞節上,美
洲的首次正教禮儀於停泊在錫特卡(Sitka)灣的聖彼得號輪船的甲板上舉行。數年以後,一大群希臘人到達佛羅里達,建立了新士麥那(New Smyrna)殖民地,但是這個冒險遭到了災難性的失敗。2
如果説正教徒流徙的事實本身不是新出現的,那也只是在二十世紀,流徙才達到使正教成為非正教國家宗教生活重要因素的程度。即使在今天,由於民族和管轄上的分隔,流徙的影響力比它本應發揮的作用要小。
在流徙的故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布爾什維克革命,它使一百多萬人被流放,其中包括國家的文化和知識精英。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包括希臘人和斯拉夫人在内的正教徒移民,大多數都是很少受教育的穷人——尋找土地或工作的農民或手工勞動者。但是在俄國革命後的流放大潮中,許多人具備在學術層面上與西方接觸的能力,能夠以大多數先前移民顯然不能的方式,將正教展現給非正教世界。在一九一七年後,特别是最初的幾年,俄羅斯移民有驚人的成果:據計算,有一萬本書籍和兩百份期刊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年間出版,這還不包括學術和科學評論。今天的西方,特别是美國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希臘人,在他們所在國家的政治學術和專業領域發揮着卓越的作用。
從宗教方面來説,正教徒移民按照強烈的民族劃分被組織起來。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早期,最初的主動權不是來自上層,而是來自下層:來自平信徒而不是高級神職人員。
一群移民聚齊起來並邀請一位來自故國的神父,一個教區就形成了。在很久以後,主教才直接參與這種安排活動。對於第一代移民來説,當地的教區教會是他們同祖國的重要紐帶,他們在這聽到自己的母語,這是他們民族風俗的方舟和衛士。因此西方的正教自開始時就具有明顯的種族特徵,其原因完全可以理解。
民族現在是上帝的禮物。索爾仁尼琴在一九七0年的諾貝爾獲獎演説中正確地指出:「民族是人類的財富,它的集體個性;其中最微小的部分都有其自己的特殊顏色具有神聖含義的特殊方面。」3
不幸的是,在流徙的宗教生活中,民族忠誠本身是合法的,它的勝利以犧牲正教的大公性為代價,這導致教會結構發生嚴重的碎片化。每個地方不是只有一個由一位主教管轄的主教教區,西方幾乎到處都發展起多重平行的管轄權,每個主要城市都同時有幾位正教主教。無論這種情況的歷史原因是甚麼,它肯定同正教的教會觀念相悖,普世宗主教迪米特里奧斯在一九九0年訪問美國時,正確地把美國正教的種族分離稱為「真正的醜聞」。今天,我們許多人都期望看到,在所有西方國家裏,一個地方教會以統一的組織方式接納所有正教徒;單個教區如果有意願就能夠保持其種族特徵,但是所有人都要承認同一地區的高級神職人員,每個國家的所有高級神職人員要在會議上共同就坐。遺憾的是,這僅僅是一個遙遠的期望。目前的情況,要超越種族分離是困難的。
除了這些種族分離,許多民族團體內部也有分裂,從屬靈方面説,它對西方正教生活的傷害比種族分離更大。除了一些緊張的地區以外,希臘移民的教會組織自一九二二年以來就或多或少聯合起來,歸於普世宗主教區之下。但是逃離共產主義的正教徒幾乎都分裂成相爭的派,一派維持同母教會的聯繫,另一派建立獨立的「流放教會」。儘管共產主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垮台了,但是大多數教派分裂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俄羅斯人流徙的故事特別複雜和悲慘。下面是四個主要的管轄區:
(一)莫斯科宗主教區,包括那些選擇同俄羅斯的教會權威維持直接聯繫的移民教區(?三萬至四萬會員,在西方各處)。
(二)俄羅斯以外的俄羅斯正教會(ROCOR);也被稱為「俄羅斯正教流放教會」、「國外的俄羅斯正教會」、「會議教會」、「卡爾洛夫茲(Karlovtsy)會議」(大約有十五萬會員)。現在的領導者是都主教維塔利(Vitaly,1986年當選)。
(三)西欧的俄羅斯正教主教大管區,受普世宗主教區管轄,也被稱為「巴黎管轄區」(大約有五萬會員)。現在的領導者是賽吉烏斯大主教(1993年當選)。
(四)美洲的俄羅斯正教希臘天主教會,也被稱為The Metropolia它在一九七0年成為「美洲正教會」(美國正教會[OCA],會員總數為一百萬)。現在的領導者是都主教迪奥多西(1977年當選)。
這種分離是怎樣出现的?莫斯科宗主教吉洪在一九二0年十一月二十日發佈一項命令,向不能同宗主教區維持正式關係的俄羅斯教會主教授權,准予他們建立自己的臨時性獨立組織。被流放的俄羅斯主教在白軍潰敗以後決定執行這項命令,而吉洪是否想要在俄羅斯疆域以外執行這項政策卻是個問題。第一次會議於一九二0年在君士坦丁堡召開;在塞爾維亞宗主教迪米特里捷(Dimitrije)的支持下,第二次會議於一九二一年在南斯拉夫的斯雷姆斯基卡爾洛夫奇(Sremski-Karlovci-[Karlovtsy])召開。一個管理俄羅斯流放正教徒的臨時組織建立起來,它位於主教會議之下,主教會議每年在卡爾洛夫茲召開。卡爾洛夫茲會議的首位領導者是曾任基輔都主教的安東尼( Antony[Khrapovitsky],1863-1936),在當時的俄羅斯高級神職人員中,他是最勇敢和最有原創性的神學家之一。一九二一年的卡爾洛夫茲會議做出一些決定,還通過一項違背許多參會者意願的提議恢復俄羅斯的羅曼諾夫王朝。
卡爾洛夫茲主教們強烈的反共產主義態度使吉洪處於一個微妙的境地。他於一九二二年下令解散會議,但主教們在實質上以相同的方式重新召開會議。卡爾洛夫茲主教完全拒絕宗主教權的「監護人」塞吉烏斯都主教一九二七年的聲明。而塞吉烏斯一方則在一九二八年宣佈卡爾洛夫茲會議的一切規定都是無效和無用的。會議總部在二戰後移到慕尼黑。自一九四九年以後就移到紐約· ROCOR於一九九0年將其工作擴展到前蘇聯,在那祝聖兩位主教,在莫斯科、聖彼得堡和各地建立教區; ROCOR的俄羅斯分部被稱為「自由俄羅斯正教會」。這一舉動顯然導致 ROCOR和莫斯科宗主教區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
ROCOR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以來逐漸被孤立,儘管它仍然同塞爾維亞教會維持着聯繫。這種分離狀態在很大程度上由於 ROCOR自己的選擇:領導者強烈地感受到,其他正教會由於參與普世運動而危及了真正的信仰。無論出於甚麼原因, ROCOR的孤立必定是很大的遺憾。它忠誠地保存了正教俄羅斯的禁慾丶修道和禮儀傳統,這一傳統靈性是西方正教徒極其需要的。
所有被流放的俄羅斯主教起初試圖同卡爾洛夫茲會議合作,但是分裂在一九二六年以後出現,這導致上面提到的第三個和第四個組織建立了。巴黎管轄區源於巴黎的俄羅斯主教伊弗洛基都主教(1864-1946),吉洪宗主教已經任命伊弗洛基為他在西歐的主教。伊弗洛基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同卡爾洛夫茲會議決裂,在一九三0年被宗主教權的監護人塞吉鳥斯否定,因為他代表蘇聯被壓迫的基督徒,參與倫敦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禱吿儀式。伊弗洛基在一九三一年向普世宗主教弗提烏斯二世求助,後者接納了他和他的教區,將之置於君士坦丁堡的管轄之下。伊弗洛基在一九四五年死前不久重返莫斯科管轄區,但是他的絕大部分信眾選擇繼續接受君士坦丁堡的管轄。儘管巴黎的俄羅斯大主教轄區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一年間遇到很多困難,但至今仍然接受普世教權的管轄。
第四個組織是北美 Metropoliao·美洲的俄羅斯人在革命後的處境同其他地方的因俄國革命造成的移民有點不同,因為在俄羅斯以外的國家中,唯有這裏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就有常設的,帶有居住主教的俄羅斯主教教區。紐約的都主教普拉(Platon,1866-1934)同伊弗洛基一样,在一九二六年脱離了卡爾洛夫茲會議;一九二四年,他就已經斷絕了同莫斯科宗主教區的聯繫,因此在一九二六年以後,美國的俄羅斯人實際上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組織。在一九三五至一九四六年間, Metropolia維持同卡爾洛夫兹會議的聯繫,但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克利夫蘭(Cleveland)會議上,大多數代表投票重新歸屬莫斯科宗主教區管轄,條件是莫斯科允許他們維持「現在這樣的完全自治」。宗主教區在那時不能同意這點。但是俄羅斯教會在一九七0年不僅允許Metropolia自治,而且允許Metropolia獨立。這個「獨立的美國正教會」 (OCA)已經得到保加利亞、格魯吉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教會的承認,但是還未得到君士坦丁堡或任何其他正教會的承認。普世宗主教區認為它同其他正教會協商行動,自己有權在美國建立獨立教會。儘管爭端尚未解決,但OCA繼續同其餘的正教會維持充分的聯絡。
二、西方的正教
我們不是要面面俱到,而是簡要地概覽西歐、北美和(更簡要地概覽)澳大利亞的正教。巴黎是西歐的主要知識和靈性中心。一九二五年在這裏建立了著名的聖塞吉烏斯神學研究院(受俄羅斯人的巴黎管轄區管轄) ,它發揮了連接正教徒和非正教徒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內戰時期,研究院的教授中湧現出一批特別傑出的學者。聖塞吉烏斯神學研究院以前的在職者中包括曾擔任第一任院長的主神父布爾加科夫(Sergius Bulgakov, 1871—1944) ;任第二任院長的主教卡西安(Cassian, 1892-1965) ;卡塔舍夫(Anton Kartashev, 1875- 1960) ;費多托夫(George P, Fedoto, 1886—1951);伊多科莫夫(Paul Evdokimov, 1901—1970) 。現有教授安德羅尼科夫( Constantin Andronikoff) 、鲍瑞斯科伊神父(Boris Bobrinskoy)和法國正教作家克莱蒙特(Olivier Clement)
聖塞吉烏斯的三位成員:弗洛羅夫斯基神父、舒梅曼(Alexander Schmemann, 1921-1983)和梅耶多夫(John Meyendorf, 1926—1992)遷居美國,他們在美國的正教發展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統計研究院的教師們在一九二五到一九四七年間出版的書籍和發表的文章,清單長達九十二頁,其中包括七十部全集,任何教會的神學研究院(無論多大)的成員取得的成果幾乎都不能與之相媲美。聖塞吉鳥斯還以其唱詩班而聞名,在恢復使用俄羅斯古代的教會讚美詩方面,它可謂貢獻良多。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它的成員幾乎全都是俄羅斯人,現在則吸引着其他許多國家的學生,主要使用法語授課。目前的全日制學生超過五十名,其他的函授學生約有四百名。
莫斯科宗主教區也對西歐的正教生活做出突出的貢獻。其神學家包括洛斯基(Vladimir Lossky, 1903—1958) ,布魯塞爾的大主教巴西爾(Basil Krivocheine, 1900—1985) ,大主教阿歷克西斯(Alexis van der Mensbrugghe, 1899-1980 ,他最初是羅馬天主教徒) 。洛斯基是弗拉基米爾的兒子,他專門研究十七世紀神學家安德魯斯(Lancelot Andrewes) ,他發挪出安德魯斯的思想中具有突出的正教傾向。4作為聖像畫家和聖像神學作家,郭斯賓斯基(Leonid Ouspensky, 1902-1987) 具有廣泛的影響力,而克魯格(Gregory Kroug, 1909—1969)通過他的作品顯示出對聖像傳統的忠誠能夠同寬廣的藝術創造力相結合。5
莫斯科宗主教教區在英國的領袖是所羅茨(Sourozh) 的都主教安東尼(Anthony [Bloom]) ,他作為一個禱告教師為備受尊敬。他的主教教區帶頭在英國使用英語做禮拜,神職人員和平信徒之間的罕見的緊密合作出現在他的主教教區年度會議上。
西方正教迄今為止很少造就出宗教音樂作曲家,但至少英國皈依者塔文那(John Tavener)是個著名的例外。他最初以創作世俗音樂出名,現在只限於創作宗教主題的音樂,創造性地嘗試將傳統的拜占庭八調讚美詩和古代俄羅斯的讚美詩轉換為一種既具有永恒性又有當代性的風格。他在其著作中歸納自己的方法,説到:「我要説,適用於所有神聖的基督教藝術的格言必定是聖保羅在另一個場合説過的話:『活着的不是我,而是我心裏的基督」。」
阿甲按:论绘画与音乐的世俗化
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与音乐开始从上帝转向世界,于是肉体更加真实,更加肉欲化「侧重于展现人体之美」,音乐更加著作个人情感的宣泄和思想的表达。而在此之前,绘画集中于圣像传统中。而圣像是传递上帝恩典和属灵世界的媒介「镜子或窗户的比喻」,圣像不会激发人的肉欲,甚至个人性的,比较表层的情感「虽然这是难以避免的」,而是因人心到上帝面前祈祷,是帮助人与上帝,与圣人们相交的。那时的音乐是圣乐,主要用于赞美上帝。中国人也有风雅颂之区分。我并不是说,绘画与音乐完全不用触及这一块,而是说不能只有这一块,不能没有一个先后次序。简单来说,圣像与圣乐是雅是颂,应该占据一个社会,国家文明的主流,主要层面,风可以表达民情,让老百姓的情绪和疾苦得以表达和舒缓,从这个意义上也是好的。但前者是主,后者是次,我们现在完全颠倒了,这就是世俗化的体现。
英國的正教特別有福,因為在埃塞克斯的奈兹(TolleshuntKnights,Essex,普世宗主教區) ,成立了一個不斷擴大的修道院團體,成員既有修士又有修女,而建立這個修道院的是修道院長所弗羅尼(Sophrony) ,阿索斯的聖西路安的學生。這裏把耶穌禱告放在中心位置。有大量朝聖者訪問這所修道院,特別是構成英國正教徒大多數的希臘塞浦路斯人。法國有兩所設施優良的女修道院,一所位於諾曼底的普魯蒙特(ProvementNormandy ,隸屬ROCOR) ,另一所位於容納省的比西昂諾特(Bussy—en—Othe, Yonne 隸屬普世宗主教區)。普拉西德(PlacicDeseille)修道院長(曾經是羅馬天主教徒)在魯瓦昂地區聖各朗(St Laurent—en—Royans)創辦兩所修道院,一所男修道院和一所女修道院,由西蒙斯,派特拉斯的安東尼修道院(Athonite House of Simonos Petras) 所支持。
西歐一位非常特殊的正教人物是身為法國人的修道院長列夫(Lev Gillet,193—1980) ,他的大多數著作都以「東方教會的修士」的名字出版。他起初是一位東儀天主教神父,在一九二八年被接納進正教,後來在倫敦做神父,為聖阿爾本和聖塞吉烏斯的的團體做禮儀。他比大多數人更好地表遠出正教會在二十世紀的矛盾:
奇怪的正教會是如此不幸和如此脆弱,同時又是如此傳統和如此自由,如此古老又如此有活力,如此禮儀化又如此個人神秘化,福音的無價之實珍識在教會中,上面有時還有一層灰尘——常常被证实為不會行動的教會卻知道如何歌唱復活節的歡樂,而其他人卻不知道。6
阿甲按:西方要回到它基督教的根源中,要学习东方教会的灵修和礼仪传统
目前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以后,科技发达,物质极大的丰富,但灵修却越来越缺乏,这是不合宜的。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科技越发达,人心越邪恶,不断世俗化的世代。若不及时回到它的灵性传统中,世俗化只会越来越严重,后果不堪设想。这就好比小孩玩火,现代最前沿的技术,例如AI,机器人等好比火,由于他心智还不成熟「即灵性软弱,还是个孩子」,容易引火上身。基督教的灵修传统是非常深厚的。无论现在的国家是什么政治体制,如果一个国家的灵修传统没有起来,就不可能持续地强盛和发展。比如当下美国,马斯克调查USAID,他们发现很多腐败现象,就是把很多钱用于LGBTQ+,和恐怖主义分子,比如HAMAS。我想这就是东方教会给西方的贡献,它们保留了这些灵修传统,现在西方不可骄傲,应该学习东方,学习东方的灵修传统,维护基督教的传统和文化,保持它的完整。不可因为这些东方教会没有对现代的科技文明做贡献就鄙视它们,这是错误的。它们保留了西方所遗弃的优秀传统——灵修传统,礼仪传统,这些西方人应该回过头来学习西方,不要只顾着发展科技,而要两者兼容并包一同发展,不然西方的陨落是不可逆转的。
北美(美國和加拿大)有三百多萬正教徒,四十多位主教,大約二千二百五十個教區,至少被劃分為十五個不同的管轄區。我們已經了解到,第一批到達美洲大陸的正教徒是俄羅斯人。一七九四年,一群來自於俄羅斯拉多加湖畔的瓦拉莫修道院的修士們在阿拉斯加(一八六七年以前是俄羅斯的一部分)建立了一個教會傳教團。斯普魯斯島(Spruce)的隱士聖赫曼(St Herman ,卒於1836年)是其中的一員,他特別受原住民的愛戴。聖英諾森(St Innocent Veniaminov)第一次為傳教工作建立了堅固的基石,他從一八二四年到一八五三年間一直在阿拉斯加工作,最初做神父,後來成為主教。他密切而同情地關注原住民的風俗和信仰,他關於這方面的著作仍然是現代民族學的重要資料。他沿循聖西里爾和聖美多迪鳥的傳統,迅速將福音書和禮儀書翻譯成阿留申語。一八四五年他在錫特卡開辦一所神學院,尋求建立本土的神父團體。他的身體強健,是不屈不撓的旅行家,歷盡艱辛展開經年之久的傳教之旅。他為了到達更加遙遠的島嶼,常常乘坐不結實的土人船隻穿越茫茫大海,照他的説法,「沒有毯子抵禦死神——只有皮膚」。
於此同時,在十九世紀的時候,許多正教徒移民一一希腊人、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阿拉伯人—在美國東海岸定居,並逐漸向西推進。許多東儀天主教徒在聖托斯(St AlexisToth, 1854—1909)的帶領下,於一八九一年後加入俄羅斯正教大主教管區,這主要是因為羅馬天主教聖統制不讓他們保留已婚的神父。未來的莫斯科宗主教吉洪在北美呆了九年
(1898—1907) ,在他的領導下,俄羅斯大主教管區開始逐漸具有跨國特徵,並且1904年,一位名叫拉菲爾(Raphael
Hawaweeny)的敘利亞人被封為他的助理主教,以照料阿拉伯正教徒。吉洪鼓勵人們使用英語做禮拜,推動出版英譯著作,特別是哈普古德(i. P. Hapgood)編譯的名著《禱告書》 。
阿甲按:人口迁徙跟政治运动,动荡以及战争息息相关。政治运动越频繁,约动荡,战争越多越猛烈,人口迁徙越大越长久。宗教的稳定发展离不可政治的稳定。在政治动荡,战争频繁的地区,宗教是不可能有良好发展的。比如说安史之乱,大概全国死了至少四分之一的人口,那么,当时的景教徒都跑到了现在的新疆和敦煌地区。很多宣教士,在政治环境不允许时,也不得不离开到东南亚国家,或者其他地方去服侍中国人。比如我认识一对美国宣教士,2019年那会政府明确告诉他们必须离开中国,于是他们离开,来到了伦敦服侍当地的华人教会。
直到一戰結束以前,俄羅斯大主教管區是北美唯一的正教組織,大多數正教教區無論有甚麼種族特徵,都依賴俄羅斯大主教及其副主教照料其教牧。雖然普世宗主教區和希臘教會從未正式接受這一安排,但教規和組織上的統一實際存在。混亂動荡的時期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接踵而來。俄羅斯人開始分裂成衝突的團體,雖然大多數人仍然留在Metropolia内。一個分離的希臘正教大主教管區在一九二二年建立,其他的民族團體及時步其後塵,建立他們自己的主教教區。目前的多種「管轄區」就這樣出現了,這種情況同樣令美國正教徒和外圍的觀察者感到困惑。
今天北美最大的正教團體是希臘大主教管區,它大約有四百七十五個教區。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內部分裂使它受損,雅典那戈拉(Athenagoras)重新組織和統一了它,一九三一至一九四八年,他是大主教,後來成為普世宗主教。一九五九至一九九六年的大主教管區領袖是雅科沃斯(lakovos)大主教,在使正教為大多數美國公眾所知和所尊敬方面,無人能出其右。面積排在希臘大主教管區後面的是OCA ,曾經的俄羅斯Metropolia,現在具有多民族特徵,主要使用英語作為禮儀用語,許多神職人員都是皈依者。面積第三大的是安提阿大主教管區(歸屬於安提阿宗主教區) ,都主教菲利普是其有力的領導者。他在一九八六年將一群前新教徒,由吉爾奎斯特(Peter Gillaquist)领導的「福音正教會」纳入正教。加拿大人數最多的正教團體是烏克蘭人的團體:按照教規來説,它被孤立了許多年,一九九一年被普世宗主教區接納。
美國的正教徒擁有十所神學學校,其中最著名的是位於紐約城外克里斯特伍德(Crestwood)的聖弗拉基米爾神學學校和位於波士頓布魯克林(Brookline) (屬於希臘大主教管區)的聖十字架神學學校。聖弗拉基米爾神學學校發行《聖弗拉基米爾神學季刊》 (St Vladimir's Theological Quarterly) , 聖十字架神學學校發行《希臘正教神學評論》 (The GreekOrthodox Review) 。今天在北美工作的正教神學家包括OCA的彼得大主教(Peter ['Huilier),聖弗拉基米爾神學學校的霍普科神父(Thomas Hopko) ,布莱克神父(John Breck) ,和埃里克森神父(John Erickson) ,安提阿大主教管區的艾倫神父(Joseph Allen) ,希臘大主教管區的匹兹堡的馬克西姆斯主教(Maximos of Pitsburg)和聖十字架神學學校的哈拉克斯神父(Stanley Harakas) 。正教修道主義發現北美在整體上是一塊堅固的領地:「修道士是教會的砥柱和基石」,如果斯托迪奥的聖西奧多的這句話是對的,美國正教的情況是不平靜的。修道生活最為強大的是ROCOR ,其中領銜的修道院是紐約約旦維爾(Jordonville)的聖三一修道院(擁有一所附屬的神學院) 。OCA擁有一所建立時間很早的修道院,它是位於賓夕法尼亞州南迦南(South Canaan)的聖吉洪修道院(也有一所神學院) 。菲羅提歐(阿索斯)的前任修道院院長艾弗雷神父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在希臘大主教管區建立了十多個小團體,其中主要是女子團體。
正教徒移民澳大利亞的時間要晚於北美的流徙,大多數澳大利亞正教教區在二戰以後建立。希臘大主教管區是最大的團體,擁有的教區超過一百二十一個,還有一所在剛在悉尼開放的神學學院。澳大利亞也有許多俄羅斯教區(主要屬於ROCOR) ,和一個重要的阿拉伯教區(歸屬於安提阿宗主教區)。
流徙正教徒面臨着兩個基本問題。首先,從第一代正教徒移民到在西方出生和成長的第二代正教徒的變遷。第一代移民即使不是始終如一地積極實踐他們的信仰,大多數情況下也會至死不渝地保持他們是正教基督徒的意識。但是第二代會怎樣?他們會繼續忠誠於他們的正教遺產,或者以不同的方式成長,被周圍的世俗西方社會同化嗎?在北美,很大一部分移民是在一戰前到達,大多數正教群體已經經歷過這個從第一代到第二代的至關重要的文化變遷;雖然損失巨大,但正教存活下來。然而在西歐和澳大利亞,移民的主體僅在二戰後才到達,這個變遷還沒有完成。
在實現變遷時,與其從祖國進口「現成的」神父,不如從在西方出生和受訓的正教徒中選拔未來的神職人員,這對於所有正教群體都至關重要。更為重要的是,禮儀崇拜要廣泛使用本地的語言———英語、法語、德語等等,否則青年人會流失,因為一個看上去對維持「古老國家」的文化和語言比對宣講基督教信仰更為關心的教會使他們疏遠。不幸的是,西方的正教領導者急於保存他們的民族遺産,在將地方語言引入到教會禮儀時常常很遲緩。北美現在廣泛使用英語,OCA、安提阿大主教管區和許多希臘教區都如此。但是英國的大多數希臘教區實則完全不用英語。
流徙面臨的第二個突出問題是它分裂成單獨的管轄區。儘管從歷史的觀點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對以下兩都造成嚴重的傷害,一方是西方正教會的教牧工作,另一方是外部世界的西方正教見證者。隨着挫折日漸增多,平信徒和神職人員都詢問:我們何時才能實實在在地統一?我們怎樣才能更加有效地證實正教的普世性?大多數西方國家建立了主教委員會(英國未建立) ,這是一個微小的開端。例如,美洲的教規正教主教常委會(SCOBA)於一九六0年在美洲大陸成立,但它未能如當初希望的那樣對正教統一做出積極的貢獻。活躍於地區的正教基督教團體遍佈美國,神職人員和平信徒都參與其中,它致力於建立跨越管轄區界限的友誼與合作。法國的博愛正教(Fraternité Orthodoxe) ,英國的施洗者聖約翰正教團體做了類似的工作。這些草根組織的潛在貢獻非常巨大,因為西方正教統一的最終實現與其説是通過全體正教會議的決議來自上層,不如説是來自上帝子民的相互之愛和不能容忍長期等待的神聖不安。
西方的正教還有一個需要特別提及的方面:西儀(Western rite)正教(在反向意義上等同於东儀天主教)的存在,儘管它是有限的和嘗試性的。在教會歷史的頭一千年,在東西方發生分裂以前,西方使用自己的禮儀,它不同於拜占庭的禮儀,卻是完全的正教禮儀。人們經常談論的「正教禮儀」其實指的是拜占庭禮儀。但是我們不能説只有它才是正教的,因為古代羅馬人,高卢人、凱爾特人和莫沙拉比人的禮儀都可以回溯到分裂以前,也都在整個正教中估有一席之地。美國和法國都有西儀正教教區,美國的西儀正教教區歸屬於安提阿大主教管區(大約有一萬名成員) ,法國的西儀正教教區有一個非常活躍的組織,名為法國天主教——正教會,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九三七年。温奈特(Louis—CharlesWinnaert, 1880—1937)曾是羅馬天主教神父,在自由天主教會內被祝聖為主教,一九三七年,他和同伴在巴黎被莫斯科宗主教區接納。7
宗主教權的監護人塞吉烏斯都主教的特別決定,允許他們繼續使用西方禮儀。溫奈特的繼任者柯瓦列夫斯基神父(Evgraph Kovalevsky, 1905-1970),在一九六四年被祝聖為聖丹尼斯(Jean de St—Denys)主教——設計了一套禮儀,這套禮儀以古代高盧禮儀為基礎,融合了拜占庭的禮儀。在現在的領導者主教傑曼(Germain)的領導下,它終止了同其他正教會的聯繫,它的未來是個問題。英國在一九九五年以後出現了一些西儀教區,歸屬於安提阿宗主教區。
流徙的正教徒是陌生環境中的少數派,他們常常發現生存就是一場艱難的鬥爭。但是無論如何,他們中的一些人認識到,除了單純的生存,他們還要應對更大的挑戰。如果他們真的相信正教是真正的大公信仰,那麼他們就不應該同他們周圍的大多數非正教徒相分離,作為一項責任和特權,他們應該同其他人分享正教。上帝讓正教徒在二十世紀散佈於整個西方,這絕不是出於偶然。這場流徙不是意外和悲慘的,相反卻構成我們的時機(kairos) 。但是如果我們按照應有的回應方式回應這個時機,我們正教徒需要做的不僅有理解還有傾聽:更深刻地理解我們的正教遺產,更謙恭地傾聽我們的西方同時代人在宗教及世俗事物上説了些甚麼。
不僅流徙區的正教缺乏相互接觸,所有不同的宗主教區和獨立教會長期以來互相孤立,雖然這常常不是由於他們自己的過錯造成的。唯一的正式接觸有時是教會領袖之間固定交換信件。這種孤立在今天仍然繼續存在,但是加深密切合作的願望正在增長。參加普世教會協會的正教徒在這裏發揮其作用:在普世教會協會的大會上,正教徒代表常常發現自己沒有準備好用統一的聲音講話。他們問道,為甚麼需要由世界大會將我們正教徒聚集在一起?為甚麼我們自己從未聚在一起討論我們共同的問題?青年運動特別感受到全體正教徒迫切需要共同合作,一九五三年建立的國際青年組織「連接」(Syndesmos)已經在此方面做了有價值的工作。
正教會的高級神職人員,普世宗主教自然在嘗試合作時發揮領頭作用。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區在一戰後考慮組織一個由全體正教會參加的「大會」,第一步計劃是組織「預備會議」以準備大會日程。一個初步的正教內部委員會一九三0年在阿索斯山成立,但是預備會議從未具體成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土耳其政府的阻撓。普世宗主教雅典那戈拉在一九五0年左右再次動了這個念頭,幾次推遲之後,一九六一年九月最終在羅得島召開了一個「全體正教會議」。羅德會議繼續在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召開,正教內部會議和委員會此後固定在日內瓦召開。如果「偉大而神聖的會議」最終召開的話,它的主要議事日程將是流徙正教的不統一問題,正教和其他基督教會的關係(普世教會主義)問題,在現代世界運用正教道德教義的問題。
三、傳教團
人們常常批評正教不能成為一個傳教教會,這個指控符合事實。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西里爾和美多迪烏及其學生使斯拉夫人飯依,就必須承認拜占庭能夠自稱其傳教成就絕不遜於同時期的凱爾特或羅馬基督教。土耳其人統治下的希臘人和阿拉伯人當然被禁止進行傳教工作,但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教會對俄羅斯帝國內的許多非基督教民族開展了大規模的傳教工作。整個傳教工作在共產主義統治下受到壓制,但是現在又在有限的範圍內恢復了。
俄羅斯的傳教工作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就擴展到俄羅斯以外,不僅擴展到阿拉斯加(我們已經講過) ,還擴展到中國、日本和韓國。無論俄羅斯傳教團走到哪裏,它的關注點之一就是儘可能地確立本土神職人員。對中國的傳教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晚期,而系統的工作直到十九世紀晚期才發展起來。大約有四百名中國正教徒在義和團運動(1901年)中殉教。當中國正教會在一九五七年進行自治時,大約有兩名華人主教和兩萬名信徒,但是「紅衛兵」在一九六六年進行的壓制迫使中國的正教徒幾乎全部轉入地下。今天,有幾位年邁的華人神父在幾個地方舉行禮儀活動,但是主教都去世了,仍然保持忠誠的信徒很少。
日本正教會由聖尼古拉斯(Kassakin, 1836—1912)建立,他是現代所有基督教團體中最偉大的傳教士之一。他在一八六一年被送到函館,做俄羅斯領事館的神父,他在一開始就決定獻身於向日本人傳播基督教信仰的工作,儘管那時的日本法律嚴厲禁止傳教工作。他在一八六八年為他的第一個皈依者洗禮,第一位日本神父在一八七五年被授聖職。當他在一九一二年去世時,日本共有二六六個團體,三萬三千零一七名成員,三十五位日本神父和二十二位執事。日本正教會在內戰時期遭受損失,但在今天大約有二萬五千名信徒,一位主教,大約四十位神父。現今的領袖是提奧多西(1972年當選)都主教,他原先是佛教徒,他同其神職人員的相同之處是,他也是日本人。日本教會是自治的,接受它的母教會俄羅斯教會的靈性照料。
俄羅斯神職人員在一八九八年建立了韓國傳教團,它幾乎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終結,但是在一位希臘神父索迪利奥斯(Sotrios Trambas)的領導下,它在二十世紀最後十五年得到復興,索迪利奧斯在一九九三年被祝聖為主教。韓國現在的教區數超過五個,還有一所神學院和一所修道院。在普世宗主教區的支持下,傳教工作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也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香港和南孟加拉(印度)開始。
除了這些亞洲的正教傳教團以外,非洲的正教會在肯尼亞、烏干達和坦桑尼亞也特別活躍。非洲正教自一開始就是本土的,它不是通過傳統正教國家的傳教士宣講才出現的,而是非洲人的自發運動。非洲正教運動的創建者是兩個烏干達本土人,饒本(Rauben Sebanja Mukasa Spartas ,生於一八九九年,一九七二年擺升主教,死於一九八二年)和他的朋友奥巴迪(Obadiah Kabanda Basajakitalo) 。他們在少年時期是聖公會教徒,二十年代皈依正教,這不是由於他們同其他正教徒進行個人接觸,而是通過他們自己的閱讀和研究。烏干達正教的教會地位起初是有些可疑的,因為饒本和奧巴迪最初同一個源於美國的組織建立聯絡,這個名為「非洲正教會」的組織雖然使用「正教」一詞,但實際上同真正的,歷史上的正教團體沒有關係。他們都在一九三二年被這個教會內一個名叫亞歷山大的大主教授予聖職,但在同一年的年底,他們開始意識到「非洲正教會」的身份可疑,他們割斷了同它的一切聯繫,並向亞歷山大宗主教區靠攏。但是只有
當饒本在一九四六年親自訪問亞歷山大時,宗主教才正式承認鳥干達的非洲正教團體,並將它置於自己的照料之下。
饒本和奧巴迪帶着極大的熱忱向他們的非洲同伴宣傳他們新確立的信仰,傳教運動迅速擴展。一個原因是由於正教傳教團雖然遣責一夫多妻制,但在實踐中對待那些已經有一夫多妻婚姻的人時,不像歐洲傳教團那樣嚴格。還有一個政治因素:在肯尼亞於一九五九年獲得獨立以前,肯尼亞正教同矛矛黨(Mau Mau)等非洲解放運動聯繫密切。在非洲人的眼中,正教基督教的一個顯著吸引力就是它同殖民者沒有聯繫。8在獨立以後,對正教傳教團的許多支持都消失了。但是非洲正教在最近組織得更好,再次開始發展。一些觀察家估計肯尼亞的正教徒數量在七萬到二十五萬之間,烏干達的正教徒數量為三萬,但是希臘的正教資料常常使用一個低得多的數字,整個東非大約有四萬名本土正教徒。坎帕拉(鳥干達) 目前有一名非洲人主教,他就是畢業於雅典大學的狄奧多(Theodore Nankyamas) 。一九九二年,烏干達有十九名本土神職人員,肯尼亞有六十一名,坦桑尼亞有七名。一九八二年在內羅畢創辦的正教神學學校大約有五十名學生。
非洲正教的自發發展對希臘和北美的希臘人正教徒具有重要影響,使他們更直接地意識到教會的傳教維度。饒本在一九五九年的希臘之行和狄奥多在一九六五年的美國之行具有廣泛的影響力,許多教區,特別是青年團體保證進行禱告和提供財政支持。人們認為非洲正教徒以此方式給予希臘正教徒的,多於他們所接收到的。
所有基督教團體都在今天面臨嚴峻的問題,但是比起絕大多數團體,正教面臨的困難也許更大。當代正教不容易「認识到處於失敗外表之下的勝利,察覺上帝在脆弱中實現自己的力量,真正的教會就在真實歷史之中。」9 但是如果弱點一目了然,許多生命的跡象也存在着。
無論教會領導者在共產主義統治之下做何妥協,正教也造就出無數殉教者和懺悔者。在共產主義消亡後的高度不穩定環境中,不僅有理由感到不安,還有理由懷抱偉大的希望。正教修道主義的衰落已經在聖山上發生了戲劇性的倒轉,阿索斯也許會成為更廣泛的修道復興的源泉。正教的靈性寶藏——例如《慕善集》和耶穌禱告——沒有被忘記,而是被越來越多地使用和欣賞。雖然正教神學家數量少,但是其中一些人常常在同西方接觸時受到刺激,正在重新發現他們的神學遺產中被遺忘但卻重要的元素。短視的民族主義妨礙了教會的工作,但是偶然的合作嘗試也出現了。傳教的規模仍然非常小,但是正教正在逐漸意識到自己的重要性。如果我們正教徒是現實而真誠的,那麼我們不能對我們教會的目前處境感到滿足或驕傲。可是,儘管正教有很多問題,表現出人性的缺點,但正教同時也能夠帶着信心和冷靜的樂觀主義期待未來。
見E. Carpenter,(新教主教(The Protestant Bishop; London,1956),357-364 ↩︎
见 《新士麦那:八世紀的希臘奥德賽》(new smyman Eighteenth Century Greek Odyssey; Gainesville, 1966) ↩︎
Leopold Labedz《索爾仁尼琴:文獻記錄》 ↩︎
見他的著作《傳教士蘭斯洛特安德鲁斯(1555—1626): 英國教會神秘神學的起源》1991 ↩︎
見Andrew Tregubov , (基督之光:格列高利·克魯格的聖像畫》 (The Light of ChristIconography of Gregory Kroug; New York, 1990) . ↩︎
引自Eisbeth Beh—Sigel, Lev ceilelt. 信的修上)》 (un Minede l Eglisd'Oriemt'; Paris, 1993) ↩︎
当温奈特被接納的時候,有人指出他只應該擔任神父職,人們認為自由天主教會封给他的主教職有效與否是有疑問的。 ↩︎
於其背景,見F. B. Welbour .(東非反叛者( (East African Rebels London, 1901 ↩︎
V. Lossky .(東方教會的神秘神學》 (The Mistical Thealogy of the Easterm Church 页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