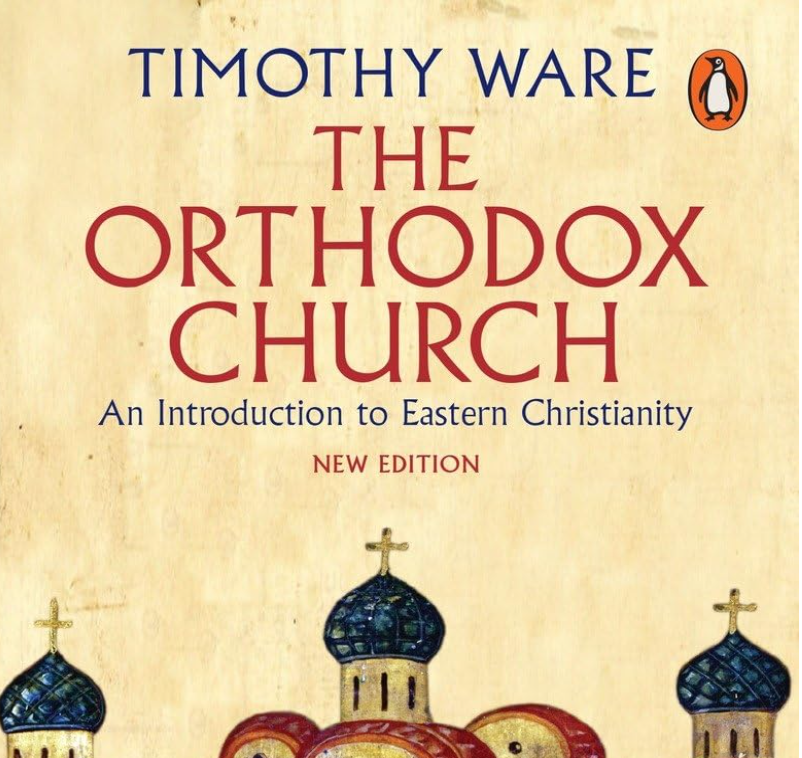-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17课,第13章 东正教崇拜上 地上的天堂。我们谈到东正教崇拜,圣像,礼仪等内容。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17课:第13章 东正教崇拜上 地上的天堂》,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5年03月28日),讲稿由阿甲整理而成,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斯斯
- 本讲稿由阿甲修订,很多内容参考这个中译本。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论》,中译田原(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若无特别说明,文字均是维尔主教的中译。若有阿甲的按语,则会写上:“阿甲按”三个字,并以引用符号标出。
油管订阅,下载音频和视频,请见这里
正文 第13章 东正教崇拜上 地上的天堂
教會是麈世的天國,天國之上帝在其中居住和活動
一一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聖日曼努斯 (St Germanus 卒於733年)
一 教義和敬拜
《俄羅斯基礎編年史)(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里有一則關於基輔王子弗拉基米爾( Vladimir)的故事,他在做異教徒時想知道甚麽是真正的宗教,因此派遣随從依次訪問世界上不同的國家。隨從首先去訪問伏爾加河畔的穆斯林保加利亞人,但是看到觀他們禱告的人像着了魔似的左看右看,俄羅斯人失望地繼續行進。他們向弗拉基米爾報告説「他們不快樂,愁容滿面,帶着很大的氣味;他們的體系沒有優良之處。」他們接下來去德國和羅馬,發現敬拜比較令人滿意,但是抱怨裹也沒有美感。他們最後到達君士坦丁堡,在这裹,當他們出席聖索菲亞大教堂的聖禮時,到底發現了他們想要的。
「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在天堂還是在世上,因為裹的壯觀和美是世上其他地方無可媲美的。我們不能向你描繪它:我們只知道上帝和人在那裹居住,他們的禮拜超出了其他所有地方的敬拜。因為我們不能忘記那種美。」
這個故事展現出正教基督教的幾個特徵。首先是對神聖之美的強調:我們不能忘記那種美。許多人認為正教徒特別是拜占庭和俄羅斯的正教徒的獨特恩賜是感受靈性世界之美的能力,和在他們的敬拜中表達那天籟之美的能力。
尘世的天国
第二個特徴是俄羅斯人説過的,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在天堂還是在世上。對於正教會來説,敬拜只是「世上的天堂」,聖禮將兩個世界合二為一,對於天堂和塵世兩者來説,禮儀是同一個一一一個聖壇,一個献祭,一個臨在。在所有的敬拜地點,無論其外觀多麽低微,當信徒在一起舉行聖餐禮時,他們就被納入「天國之地」;在所有的敬拜地點,當獻上聖祭時·臨在的不僅有當地的會眾,還有普世教會聖徒、天使、聖母和基督本人。「天國的權能現在與我們同在,以不可見的方式敬拜。」1我們知道,上帝就停留在那裏的眾人當中。正教徒被這「世間天堂」的景象所鼓舞,努力使他們的敬拜在外在的壯觀和美麗方面,成為天國宏偉聖禮的聖像。
阿甲按:论东正教崇拜之美。这是描述东正教礼仪的一个场景。如果你有机会参加过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仪式,确实会感受到其中的美。当然,如果我们受众中的大多数基督徒没有机会参与的话,我建议你们去体验一次,特别是大斋期(复活周)或圣诞节这样的重大节日时,他们的礼仪之美尤为明显。当然,并不是说天主教没有类似的情况。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金银、装饰、鲜花都被装点在教堂里面。无论是你的眼睛看到的还是耳朵听到的,甚至是鼻子闻到的,都会给你带来一种独特的体验。这种体验在新教中是体会不到的。当然,我没有参加过天主教的仪式,但你会感受到巨大的差异。有些新教徒转为正教徒就是因为参加了东正教的礼仪,他们的经历与这位基辅王子的经历很相似。我在HCHC时,问一位从新教转成正教徒的同学,:“你是怎么变成正教徒的?”他说,他们最初对新教有些不满,所以想尝试其他教会。有一次,他们参加了一个东正教的礼拜仪式,觉得这种感受与他们的内心非常契合,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被提升到了天上。因此,他们最终加入了东正教。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这种因为参加东正教礼仪而加入东正教的现象不是一个传说,它是一个事实,并且现在也在发生。
聖智慧大教堂在六一二年有八十名神父,一百五十名執事,四十名女執事,七十名副執事,一百六十名朗誦者,二十五名領唱者,一百名守門人:弗拉基米爾的使者參加的禮拜之壯麗由此可見一斑。但是不止那些基輔的俄羅斯人,就連在
大相迥異的外部環境下經歷正教敬拜的許多人都感覺到上帝臨在於人類中。例如,我們從《俄羅斯基礎編年史》轉向一封由一位英國女子在一九三五年寫的信,信上説: 這個早晨是如此奇特。在車庫後的一條小巷裏,有間非常污穢骯髒的長老會傳教大廳,俄羅斯人被允許每兩周在那裏舉行一次禮儀。一座很像舞台道具的聖像和不多的几幅现代圣像。
1.在預先聖化禮儀的大入禮上所唱的歌詞。
跪地的地板肮脏,長木凳靠在墙边…厅裹有两位優秀的老年神父和一位執事,香雾袅袅,聖餐禮的奉献儀式给人一種非常有震憾力的超自然印象。2
弗拉基米爾的使者的故事還展示出正教的第三個特徵。當俄羅斯人想要揭示真正的信仰時,他們沒有詢問道德規則或要求合理的教義聲明,而是觀察不同的國家在禱告時的情形。正教對於宗教的進路基本上是禮儀的進路,它在神聖敬拜的背景下理解教義:「正教」一詞應該同様指示正確的信仰和正確的敬拜,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兩者不可分離。
阿甲按:论地上的天堂,论象征主义。在东正教圣餐礼的举行过程中。这是他所说的地上天堂的概念,因为地上和天上一同庆祝这一胜利。从内在的角度来说,他的美丽在于即使没有出生在天上,却依然拥有天上的光辉;而从外在来看,他们确实有很多装饰,比如在过年过节时摆放的鲜花,给福音书上添加一些金边,圣像撒上金粉进行装饰。这是为什么呢?这涉及到一种叫象征主义的理念。这种象征主义对传统教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来简单评论一下象征主义的起源。比如,象征主义的一个来源是六到七世纪的一位著名教父——狄奥尼修斯。在国内,现在有一个译本《神秘神学》,已经将他的大部分著作翻译过来。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天阶秩序”。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狄奥尼修斯对传统教会最大的贡献不是来自于他关于神秘神学或《论圣名》的两部著作,因为许多学者喜欢研究这两本书籍,因为它们的语言与老子的相似,容易引起学者的兴趣。对我来说,《神秘神学》其实更像是老子之后对于“道”的另一种表达,即道可道非常道。在传统教会中,他真正留下深刻影响的是其神圣的天阶秩序——即象征主义中的天阶秩序概念。就是任何地上的物质东西,如姿势、圣像、声音、香气都有属灵的含义在象征着。因此,例如教堂如何建造,墙壁的位置在哪里?应该使用什么材料?何时开始使用香炉,以及声音出现的时间?在仪式中应进行哪些动作和姿势?这一切都体现了天阶秩序的概念。即地上的礼仪都是通过这种象征的方式来模拟天上的崇拜的,因为这地上的崇拜与天上的崇拜是同一个不是两个。就是说,通过象征可以传递上帝的恩典。我之前也给大家说过我的个人经历:有一次我在学校的时候参加他们的庆典。他们拿着香炉从中间过道走过,经过时,香味直接吸到鼻孔里。吸进鼻孔后,平时闻到的只是香味,但当时我的感受是直入心扉。当然,对于一些弟兄姊妹来说,这被称为体感福音,即领受上帝恩典的方式不仅仅是通过心思或心灵的感受,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都是可以领受神恩的「因为道成肉身」。人可以通过这些象征的方式感受到上帝的恩典。这种教导主要来自于迪奥尼修斯的《天阶秩序》一书。我认为这是他对这一领域做出的一个比较大的贡献。然而,并不是说在早期教会中没有这样的概念,只是它的影响较大。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新教没有这些东西: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是因为新教的创始人之一马丁·路德不太喜欢迪奥尼修斯这个人,所以新教把很多这类东西都去掉了。圣象、香、钟声等全部都没有了。这就是它的外在美丽的原因所在。那么,这种美丽的神学依据在哪里呢?就是地上天堂的概念。当我们讲到下一个概念——离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临在感。
「對於他們,教條不僅是由神職人員理解並向平信徒詳述的知識體系,還是一個視域,根據世間萬物同天上事物的關係來看待世間萬物,獲得這個視域,首先和最重要的是通過舉行禮儀」,對拜占庭人這個説法符合實際。用弗洛羅夫斯基的話來説,「基督教是一個禮儀的宗教。教會首先是一個敬拜團體。敬拜排在第一位,教義和紀律排在第二位。」那些希望了解正教的人與其讀書,不如延循弗拉基米爾的隨從的例子和參加禮儀。就像基督對安德烈説的:「你們來看」(約1:39)。
正教認為人首先是禮儀的造物,當人在榮耀上帝時是最真實的自己,人在敬拜中發現自己的完善和自我實現。正教徒將他們的整個宗教經驗傾注在表其信仰的神聖禮儀中。禮儀激發出他們最優秀的詩歌丶藝衠和音樂。
阿甲按:对于东正教来说,正确的崇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时,这也造成了一定的张力,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天主教会中,可能有人会认为俄罗斯那次因为一个手势就分裂出一个旧礼派来感到惊奇,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礼仪分裂”,天主教徒是难以理解这种现象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正教的很多教导无法在细节上明确下来,比如维尔主教这本书很多没有明说,就是分界线还没有明确下来;另一方面,对于东正教礼仪的更改要十分小心,因为在很多正教徒看来,就是更改礼仪「哪怕一个姿势」与更改教理几乎是一码事。因为正教徒认为正确的教理是通过正确的礼仪得到展现的。你修改了礼仪文本,甚至唱词风格,礼仪中的姿势和动作,都有可能引发一次教会分裂。虽然,正确的教导和正确的崇拜不可分割,但我们需留意到正教内部的这种张力。
2.《安德希爾書信》( The Letters of Evelyn Underhil)頁248。
3. George Every(拜占庭宗主教區》( The Byzantine Patriarchate; London,1947)
4.《正教大公教會的禮儀因素)( The Elements of Liturgy in the Orthodox Catholic Church)
正教徒的禮儀從未像西方中世紀的禮儀那樣,成為有學問的人和神職人員所专有的,它是大眾的——為所有基督徒所共有:
正式的正教平信徒敬拜者在最初的童年即熟悉教會,他們在教堂裏完全輕鬆自在,徹底熟知聖禮中能聽到的部分。带着無意識和非研究的輕松參與禮儀活動,其程度只有西方極度虔誠的基督徒的心靈才能達到。5
在他們歴史上的黑暗時代一一處於蒙古人,土耳其人或共產主義者統治下一一正教徒始終向聖禮尋求激勵和新希望;他們從未徒勞無獲。
二、禮拜的外部環境:神父和信眾
正教禮拜的基本模式同羅馬天主教會相同:首先是聖禮(聖餐禮或弥撒);第二是日课(例如晨禱和晚禱這兩個主要的禱告,還有子夜禱告,第一,第三、第六和第九小時的禱告,晚禱);6第三是場合性祷告一一即用於洗禮·婚姻,修道認信,皇室加冕,教會的祝聖丶死人的葬禮等特殊場合的禮拜。除了這些,正教會使用非常多的較小的祝福
許多聖公會的教區教會和幾乎所有的羅馬天主教教區教會,每天都施行聖餐禮,而今天的正教會除了在座堂和大修道院,很少每天施行禮儀。但是在當今俄羅斯,儘管敬拜地點很少,而且許多基督徒被迫在主日工作,許多城鎮教區卻開始每天施行禮儀。
阿甲按:对正教徒来说,礼仪生活就是灵修生活;礼仪本身,正确的崇拜就是对上帝正确的一种回应。因为教理跟灵修和礼仪生活是不可分割的。在我教导过程中,遇到一些新教弟兄姐妹的问题后,我逐渐意识到这点,简单来说,一个人怎么信,他就会怎么生活,一个怎么生活也会影响他怎么信。举个例子,在东正教的崇拜中,他们每周日都会诵读尼西亚信经,每次早晚祷都会读尼西亚信经。然而,在我参加过的所有新教崇拜中,从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信经应该时常阅读,就像拿出真钞观摩一般,久而久之,人就能对信经的内容产生理解,就像水浸入一样,他会对异端思想有敏锐的洞察力,就像真钞看熟了,一看到假钞就知道它是假的。我们新教徒没有这种警惕性,平信徒容易受迷惑就跟这个有关。再比如,传统教会的礼仪文书都是经过好几百年的千锤百炼,逐渐完善发展而成,如果允许信徒私自形成并使用各自的礼仪文本,就可能形成很多教派了。因此,在传统教会,礼仪文本是不允许平信徒自己来编辑创作的,而是由主教们形成委员会,经过多次会议和修订才形成的,即便是翻译成其他语言也需要这个过程。再比如,将因信称义的教导等同于救恩「甚至形成一旦得救,永远得救的教导」就极大地损害了信徒过灵修生活的积极主动性。
阿甲按:那么新教要不要回到这些传统教会的教导呢?肯定需要的。否则新教就完了,除了回到传统教会的资源和教导中,至少我没有看到任何出路。因为在世俗化的倾向上,新教是最早,最容易受影响的,比如说同性恋牧师的存在,给同性婚姻祝圣等。我尤其反对新教徒敌视传统教会,自诩为义,谴责所有传统教派为异端的做法,在我看来,这种态度无意于自杀,不给自己留活路。我接触过一些喜欢我们平台的新教徒,他跟我说,他只是自己偷偷来看我们光从东方来的网站,不敢跟他们的牧者说。显然,这些牧者们是禁止他的会众来我们平台学习的。我完全不赞同这种做法,如果信徒有灵性需要,而他所在的教会无法提供这些,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平台,让他们可以大口大口地吸取早期教会和圣人们的属灵资源呢?总之一句话,新教应该回到传统教会这些丰丰富富的灵性资源和礼仪文书当中,而不是抛弃它。
正教會在禮拜中使用信眾的語言:在安提阿用阿拉伯語言。
5. Austin Oakley《正教禮儀》( The Orthodox Liturgy; London,1958)页12。
6.在羅馬的儀式中,子夜禱告( Nocturns)等同於拜占庭的子夜禱告Midnight Office是晨禱( Matins)的一部分,但是在拜占庭儀式中,子夜祷告是分開的禮拜,拜占庭的晨禱等同於羅馬儀式的晨禱和讚美禱文。
在赫爾辛基用芬蘭語,在東京用日語,在倫敦或紐約(根据需要)用英語。正教傳教士一一從九世紀的西里爾和美西狄乌,到十九世紀的維尼阿米諾夫( Innocent Veniaminov)和卡金( Nicolas Kassatkin),他們的最初任務之一,是將禱告書翻譯成當地的語言。可是在實際上,使用當地語言的一般原則出現了部分例外;講希臘語的教會不使用現代希臘语,而使用《新約》和拜占庭時代的希臘語,俄羅斯教會仍然使用中世紀的教會斯拉夫文譯本。許多俄羅斯主教其實在一九0六年建議或多或少地普遍用現代俄文代替教會斯拉夫文,但是在這個計還沒來得及實施,布爾什維克革命就爆發了。
今天的正教會和早期教會一様,所有禮拜都被歌唱或唱颂出來。正教沒有羅馬的「小禮彌撒」或聖公會的「説颂」( Said Celebration)。就像在每次晨禱和晚禱,每次禮儀都要燃香,即使沒有唱詩班或會眾,而只有神父和一位朗讀者,禮拜也被唱出來。在教會音樂方面,講希臘語的正教徒繼續使用古代拜占庭的八「調」無伴奏唱頌。拜占庭傳教士將這種無伴奏唱帶入斯拉夫大陸,但是它歴經數個世紀後得到很多修改,不同的斯拉夫教會都發展出教會音樂的各自風格和傳統。在這些傳統中,俄羅斯傳統最為著名,對西方人最有直接吸引力;許多人認為俄羅斯教會音樂在所有基督教世界中最為優秀,俄羅斯和俄羅斯移民中都有著名的俄羅斯合唱團。直到晚近時期,正教會的所有歌唱通常都由合唱團完成;在希臘俄羅斯,羅馬尼亞和流徙人群的少數但數量漸增的教區中,會眾唱歌在今天開始復興一一如果不是貫穿整個禮拜,那麽無論如何也是在信經和主禱等特殊時刻。除了如今愛好上風琴或簧風琴的一些美國正教徒,特別是其中的希臘人以外,今天的正教會同早期教會一様,唱歌無伴奏,沒有器樂。大多數正教徒不使用教堂内的手鈴或聖堂鈴,但他們有外面鐘樓,非常樂意不僅在禮拜前,而且也在禮拜的不同時刻敲鐘。俄羅斯的鐘聲在過去非常有名。阿勒頗的保羅( Paul of Aleppo)在一六五五年訪問莫斯科時寫道:「沒有甚麽東西給我的震撼像主日前夕,重大節日和節日前子夜時所有的鐘都敲響,鐘聲匯成一片那様。大地和所有的鐘一起振動,鐘聲如響雷一様,響徹天空。」「他們按照慣例敲黄銅鐘。願上帝不會被這聲音的喧鬧歡樂所驚擾!」7
阿甲按:钟楼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这是用来提醒人们参加礼仪的。因为在古代,没有手表,人们不知道哪个时间点应该做早晚祷。所以,每个镇都有一个教堂,每个教堂都有一个钟。因此,在早上的时候,他们会敲钟几下,让人们停下手中的工作来参加早祷。教会的钟楼实际上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时钟的一个来源之一,最初是用来提醒人们参加早祷,晚祷的。这段描述了当时在俄罗斯的情况。1655年,教堂的钟声对人们的生活节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几乎是核心地位。人们的日常作息是通过教堂的钟声形成的。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情况几乎消失了,因为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工业模式和经济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教教堂的設計通常幾乎都是方形的,穹頂下面覆蓋宽阔的中央場地。(在俄羅斯,教堂的穹頂是突出的洋葱形状。這形成了俄羅斯各地風景的獨特特徴。)哥特風格的座堂和更大的教區教堂普遍有細長的中堂和聖壇,這在東方的教堂建築中看不到。過去,雖然教堂的牆邊或許會有長凳或座位,但是沒有在中部放置椅子或教堂長椅的習慣;整個教堂塞滿成排的座位在近些年成為日漸顯著的趨勢,希臘和流徙人群中也有這趨勢,這令人悲哀。雖然正教徒在教堂禮拜的重要部分中保持站立仍然是標準做法(年長女性可以毫無倦容地站立幾個小時,非正教徒參觀者看到這種情形,通常很驚訝);但是會眾有時能夠坐下或跪下。第一次大公會議的第二十條教規禁止在主日和從復活節到五旬節期間的任一天下跪,但不幸的是這條規定在今天始終沒有得到嚴格遵守。
有或沒有教堂長椅,對基督教敬拜的整體精神會造成巨大的差別,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正教敬拜具有靈活性。不自知的非正式性,這一點在西方會眾中找不到,在阿爾卑斯山以北無論如何都找不到。西方敬拜者按行排列整齊全部各就各位,在禮拜時走動會擾亂別人;西方會眾通常在開始時到達並待到最後。但是正教敬拜者的來去要自由得多。
7.《馬喀里行記》( The Travels of Macarius;ed. Ridding),頁27
如果他們在禮拜中走動,沒有人特別驚訝。神職人員的行為也具有同樣的非正式性和自由:禮儀活動沒有西方那様的繁文缛节,神父的姿勢不那麼固定而是更加自然。非正式性有時雖然會導致不敬,但到底是一項寶貴的品質,正教徒如果失去它會極為遺憾。他們在教堂中舒適自在一一不是士兵在隊列場上,而是兒童在父親的家中,正教敬拜常常被稱為「他世的」,但是被稱為「家庭的」會更真實:它是一項家庭事務。在家庭性和非正式性後面隱藏着深深的神秘感。
所有正教教堂都用聖障把聖堂和裏面隔開。聖障是一道實心的屏風,通常用木質材料,上面全是鑲嵌的聖像。在早期,聖壇僅由一道三四英尺高的低矮屏風隔開。屏風頂上有時會有一排數目不定的柱子,柱子上面托一根横木或過樑。
這種屏風現在仍然能夠在威尼斯的聖馬可教堂裏看到。只有在相對晚近的時期一一在許多地方直到十五或十六世紀一一這些柱子之間的空隙被填滿,聖障具有了現在的實心式様。
許多正教禮儀專家在今天高興地延循克朗斯塔特的聖約翰的例子,恢復更加露空的聖障樣式;这在許多地方已經實現了。
聖障上有三處門。中央的大門一一神聖或皇室之門。開啟時可以看見聖壇。這處門是兩個門屙開關,後面掛着簾子。除了復活節那一周,凡不舉行禮拜時,都關閉大門,拉上簾子。在禮拜的特定時刻,門有時開敝,有時關閉,偶爾當門關閉時簾子也是關閉的。可是許多希臘教區現在在禮儀的任何時刻都不再關門或拉簾子;許多教堂都把門属去掉,
而其他教堂採用正確得多的禮儀程序一一保留門但是移走簾子。其他兩處門,左邊的通向準備聖餐( Prothesis)或做準備的「小教堂」(这裹保存聖皿。禮儀開始時神父在這裏準備餅和酒);右邊的通向「聖物房」( Diakonikon)(現在
通常用作法衣室,但最初是保存聖書,特別是福音書,和聖徒遺物的地方)。除了在禮儀中服務等特殊原因,平信徒不被允許走到聖障後面。正教教堂中的聖壇——被稱為聖台或寶座——沒靠着東牆,位於聖堂的中央;主教的寶座抵着牆,放在聖壇後面。
正教教堂裏滿是聖像一一屏風上,牆上,特殊的神龕裹,或某種桌子上,聖像能在那裏受信徒崇敬。正教徒走進教堂第一個行動就是買一根蠟燭,走到聖像前,在胸前畫十字架,親吻聖像,在聖像前點燃蠟燭。英國商人錢德勒( Richard
Chancellor)在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訪問俄羅斯,他評論説:「他們是偉大的蠟燭供應者」。在教堂的装飾上,不同的聖像畫場景和人物不是偶然安排的,而是根據了確定的神學主題,所以整個建築物成為上帝國的一座偉大圖像或形象。正教宗教藝術和西方中世紀宗教藝術一様,有着詳盡的符號體系,包含教堂建築及其装飾的所有部分。圣像·壁畫和馬賽克不僅是使教堂「好看」的装飾,還要實現神學和禮儀功能。
填充教堂的聖像作為天堂與麈世的交匯點發揮作用。當所有地方的會眾在每個主日祈禱時,當他們被基督、天使聖徒等人物包圍時,這些可見的形象無休止地提醒信徒,整個天堂不可見地臨在於禮儀中,信徒能夠感受到教堂的牆壁向永恒打開,有助於他們認識到他們在世上的禮儀同天堂的偉大禮儀是同一個。大量的聖像形象地表達了「世間天堂」的感覺。
正教會的敬拜是集體的和大眾的。比較頻繁地參加正教禮拜的任何非正教徒,會迅速認識到神父和信眾的整個敬拜團體是多麽緊密地聯接成一體;至於其他事物,教堂長椅的缺失有助於創造統一感。雖然大多數正教會眾不加入歌唱,但是不應該認為他們不在禮拜中發揮真實的作用;聖障——即使是現在的實心形式一一也不使人感覺同聖堂的神父相隔。無論如何許多禮儀在屏障前面舉行,會眾完全看得見。
大多數的正教敬拜都具有一種穩緩和永恒的品質,這個效果在部分上是由於反覆重複總祷文( Litanies)造成的。無論總禱文是長還是短,它在拜占庭的所有禮儀中都要重複幾次。在這些總禱文中,執事(如果沒有執事,就由神父)要求人們為教會和世界的不同需要而祈禱,對於每次重複,唱詩班或人們都要回答説仁慈的主一一希臘文是 Kyrieeleison,俄羅斯文是Gospodi pomilui——這也許是訪問者掌握的第一句正教禮拜詞語。(在某些總禱文中,回答變為赐予這個,主。)通過劃十字架和鞠躬,會眾使自己與不同的代禱聯起來。一般來説,正教徒使用十字架符號要比西方敬拜者頻繁得多,甚麽時候使用也更為自由:不同的敬拜者按照自己的意願在不同的時候劃十字架,當然也有所有人在禮拜中幾乎同時劃十字架的時候。
我們剛才把正教敬拜形容為永恒和穩緩的。大多數西方人認為,拜占庭的禮拜即使並不真是永恒的,無論如何也是漫長到了極點,不可忍受。比起西方來,正教的功能肯定傾向於更加延長,但是我們不應該誇大其辭。在一個小時十五分鐘裏舉行拜占庭禮儀和進行簡短佈道,是完全可能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在一九四三年規定,他管轄的教區不應舉行超過一個半小時的主日禮儀。俄羅斯人的禮拜在總體上比希臘人的長,但是在正式的俄羅斯移民教區,主日晚上的守夜祈禱禮拜不超過兩個小時,通常比兩個小時更短。修道禱告當然更長,聖山在重大節日時的禮拜有時不間斷地持續十二,甚至十五個小時,但這是例外情況。
非正教徒會對這個事實感到鼓舞:正教徒常常同他們一樣怕禮拜太長。阿勒頗的保羅訪問俄羅斯時在日記中寫道:
「我們現在進入陣痛和痛苦,因為他們所有的教堂都沒有座位。甚至連主教也沒有座位;你看見所有人在整個禮拜過程中像磐石一様紋絲不動地站立着,或者専心於虔識之中。上帝在祈禱·聖歌和彌撒中幫助我們,因為我們遭受巨大的痛苦,以致我們的靈魂被疲勞和痛苦所折磨。」他在聖周的中間欢呼説:「上帝賜予我們特别的幫助來度過現在一整周,至於莫斯科人,他們的腳必定是鐵打的。8
8.同上,頁14和直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