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在读博士:俄罗斯东正教朝圣游
按:王潇在读博士向您介绍俄罗斯朝圣游。他在俄罗斯待了十年时间,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拜访了不少教堂。特此感谢他的无私分享。Enjoy! 若要引用本文,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观看以及下载,请见主页
按:王潇在读博士向您介绍俄罗斯朝圣游。他在俄罗斯待了十年时间,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拜访了不少教堂。特此感谢他的无私分享。Enjoy! 若要引用本文,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观看以及下载,请见主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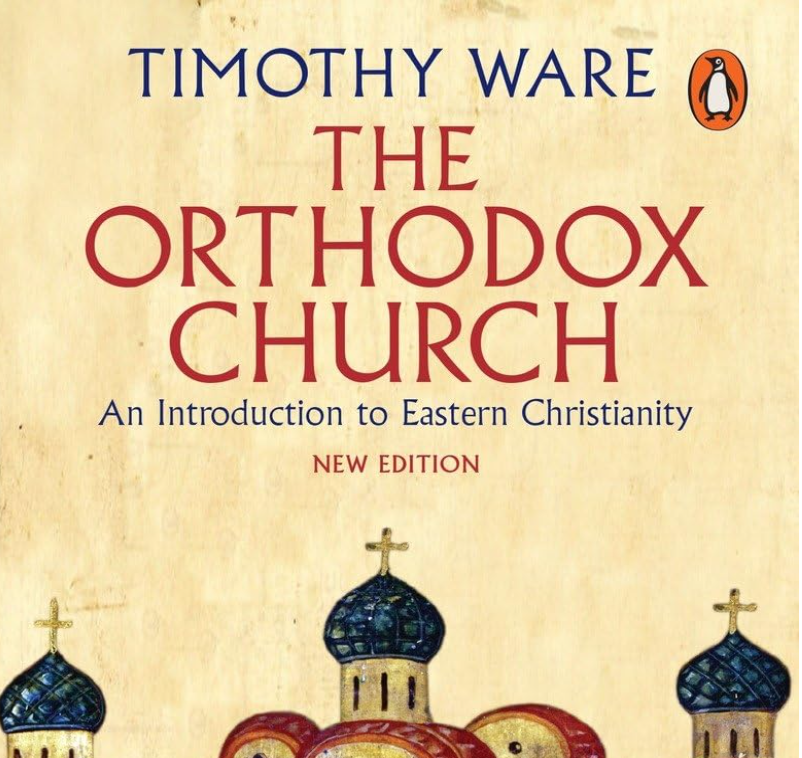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十课 俄罗斯与圣彼得堡。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10课:俄罗斯与圣彼得堡》,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11月29日),讲稿由阿甲整理而成,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斯斯 本讲稿由阿甲修订,很多内容参考这个中译本。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论》,中译田原(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若无特别说明,文字均是维尔主教的中译。若有阿甲的按语,则会写上:“阿甲按”三个字,并以引用符号标出。 油管订阅,下载音频和视频,请见这里 正文 第6章 俄罗斯与圣彼得堡 阿甲按:本章介绍莫斯科15世纪的兴起,时段涵盖15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莫斯科自诩为第三罗马,自从其发端就具备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俄罗斯的圣人传记传统。介绍了拥有派和非拥有派,旧礼派,宗主教时期「大约持续一个多世纪」、以及彼得大帝开创的圣会议时期「直到20世纪初」、以及俄罗斯的长老传统。 一、第三羅馬莫斯科 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後,只有一個國家能夠擔任東部的基督教世界的領導。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的大部分已經被土耳其人征服,而餘下的領土也在不久之後被吞併。基輔主教區歸順了波蘭和立陶宛的羅馬天主教統治者。只有俄國保持原様。在拜占庭帝國終結的特殊時刻,俄國人自己最終拋掉了韃靼宗主權僅存的殘餘:神似乎賦予他們以自由,因為他已經選中他們擔當拜占庭的繼任者,對於莫斯科人來説,這絕非偶然。 同莫斯科的國土一樣,莫斯科教會與此同時赢得了獨立,與其説獨立源於任何有目的的計劃,不如説源於偶然。在那時,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已經任命了俄羅斯教會的領袖,都主教。佛羅倫薩會議上的都主教是一位希臘人依西多(Isidore)。依西多領頭支持與羅馬聯盟,他在一四四一年返回莫斯科,公佈了佛羅倫薩會議的決議,但卻沒有得到莫斯科的支持:他被大公關進監獄,過了一段時間後逃回意大利。首要主教職因此空缺,但是俄羅斯人不能請求宗主教再派來一位新的都主教,因為君士坦丁堡的官方教會在一四五三年以前一直接受佛羅倫薩聯盟。俄羅斯人不願意自己採取行動,這種情況延續了數年。在沒有君士坦丁堡參與的情况下,於一四四八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俄羅斯主教會議最終選舉出一位都主教。在一四五三年以後,也就是在君士坦丁堡放棄佛羅倫薩聯盟以後,宗主教區和莫斯科之間的聯絡恢復了,但是俄羅斯人繼續自己任命自己的總主教。莫斯科教會自此獨立。然而,基輔都主教區繼續接受君士坦丁堡的管轄,到一六八六年轉歸莫斯科管轄,儘管這一事件沒有得到普世宗主教的任何正式祝福。 一椿婚姻推動了莫斯科充當拜占庭繼任者的念頭。伊凡三世大帝(1462—1505年在位)在一四七二年迎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亞。雖然索菲亞有兄弟且不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但是這椿婚姻起到了同拜占庭建立王朝聯繫的作用。莫斯科大公開始採用拜占庭的「獨裁者」和「沙皇」(Tsar)(羅馬文「凱撒」 [Caesar]的改稱)的稱號,開始把拜占庭的雙頭鷹用作國徽。人們開始把莫斯科視為「第三羅馬」。(他們認為)第一羅馬已經落入蠻族之手並因此瞳入異端;第二羅馬君士坦丁堡又在佛羅倫薩會議上堕入異端,受到了被士耳其人攻佔的懲罰。莫斯科因此承接君士坦丁堡,成為第三和最後的羅馬,成為正教基督教世界的中心。普斯科夫(Pskov)的修士菲洛修斯(Philotheus)在一五一0年寫給沙皇巴西爾三世的一封著名的信中,陳詞如下: 我想為我們當今的正教帝圆的統治者添加一些间語:他是世上基督徒唯一的皇帝(沙皇) ,是不再位於羅馬或君士坦丁堡,而是位於被賜福的城市莫斯科的使徒教會的領袖。在整個世界中,她的光芒比太陽還要明亮……所有的基督教帝國都淪陷了,代替他們的只有我們統治者的帝國,她符合先知書。兩個羅馬已經淪陷了,但是第三個矗立着,永遠不會有第四個。1 1.引自 Baynes&Moss《拜占庭:導論》页385 莫斯科擔當第三羅馬的想法同沙皇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相稱的:拜占庭皇帝曾經充當正教的捍衛者和保護者,現在俄羅斯的獨裁者受命承擔同樣的任務。在宗教領域,它的含義受到更多的限制,因為俄羅斯教會的領導者從未取代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在正教領導者中至多排第五位,排在耶路撒冷宗主教之後。 拥有派和非拥有派 儘管聖塞吉烏斯的夢想———俄羅斯擺脱韃靼人的統治獲得獨立的夢想變成了現實,但是在他的靈性後裔中出現了令人悲哀的分裂。塞吉鳥斯已經將修道主義的社會方面和神秘方面結合在一起,但是到了他的繼任者們那裏,這兩方面又分離了。在一五0三年的教會會議上,分裂第一次公開。當會議接近尾聲時,來自伏爾加河畔深處森林的一所隱修院的修士,索拉的聖尼魯斯(St Nilus of Sora[Nil Sorsky],?1433-1508),起立發言並對修道院土地的所有權發起了攻擊(當時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俄羅斯土地屬於修道院)。沃洛克拉姆斯克( Volokalamsk)的修道院院長聖約瑟夫(St Joseph,1439-1515)為修道院的土地所有權做了辯護。參加會議的大部分成員支持約瑟夫,但是俄羅斯教會還有一些人贊同尼魯斯——主要是像他一樣居住在伏爾加河畔深處的隱士們。 約瑟夫那一派被稱為「擁有者」,尼魯斯和「跨越伏爾加河的隱士們」被稱為「非擁有者」。雙方的關係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裹相當紧張。最終在一五二五至一五二六年,非拥有者派們抨擊沙皇巴西爾三世的離婚不正當(正教會准予离婚,但是僅出於特定原因),沙皇囚禁了非擁有者派的首领,关閉了伏爾加河那邊的隱修院。聖尼魯斯的傳統被迫轉入地下,雖然它始終沒有完全消失,但它對俄羅斯教會的影響力受到很大的限制。擁有者派在此時的境况達到了顶峰。 隱藏在修道院財產問題背後的是两種不同的修道生活概念,最終是兩種不同的教會與世界關係的觀點。擁有者派強調修道主義的社會義務:修士工作的一部分是照料病患和窮人,以顯示殷勤和教育感化,為了有效地進行這些工作,修道院需 要金錢·因此他們必須擁有土地。修士(據他們聲稱)沒將財富用於自身,而是為其他人的利益託管財富。約瑟夫的追隨者中流傅這樣一句名言:「教會的財富就是窮人的財富。」 另一方的非擁有者派聲稱救濟是平信徒的責任,而修士的首要任務是通過禱告和樹立榜樣幫助他人。為了正確地做這些工作,修士必须同世界相分離,只有那些立誓徹底貧窮的人才能實現真正的分離。當了地主的修士免不了同世俗事務糾纏,他們以世俗的方式行動和思考。用尼魯斯的學生修士瓦西安(派特基夫王子)的話來說: 在福音,使徒和教父傅统中,修士們奉命夺取村庄,從农民到教友都是奴役對象。。。。。我們窥视富人手中的东西,为了从他們那里得到小小的村莊,奴隸般的向他們奉承和谄媚。。。。。。。我們犯下错误,劫掠和出卖基督徒, 我們的兄弟。我們像对待野兽那样用鞭子鞭挞他們。2 2.引自B. Pares,《俄羅斯歷史) 瓦西安對酷刑和鞭子的抗議将我們带至雙方的第二個分歧點:如何對待異端。约瑟夫支持的觀點幾乎為當時的基督教世界一致持有:如果异端顽固不化,教會必须召集國内的軍隊,使用監獄酷刑,如果必要的話使用火刑。但是尼鲁斯譴責加諸異端的所有形式的脅迫和暴力。人們只有回憶西歐宗教改革時期的新教徒和罗馬天主教徒的相互關係,才能認識到,尼鲁斯的寬容和他對人類自由的尊重是多麼的特立獨行。 異端的問題又涉及教會和國家關係的更大問题。尼魯斯認為異端是靈性事務,應由教會解決,不需要國家介入;約瑟夫訴諸於世俗權力的幫助。大體而言,尼魯斯在歸凱撒的和歸上帝的之間劃出的界限比約瑟夫更為清晰。擁有者派極力支持莫斯科充當第三羅馬的理念,相信教會和國家之間的親密聯盟,他們像塞吉烏斯一樣積極參與政治,但是在保衛教會使之不致成為國家僕人方面,他們也許不如塞吉烏斯慎重。非擁有者派一方對修道主義的預言和他世見證有更深刻的認識。約瑟夫一方面臨着將上帝之國等同於世上王國的危險;尼魯斯認為世上的教會必須始終是朝聖的教會。約瑟夫及其派别是偉大的爱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非擁有者派更多地想到教會的普遍性和大公性。 雙方的分歧沒有在此處結束:他們也有着不同的基督教虔誠觀和禱告觀。約瑟夫強調規則和紀律的重要性,尼魯斯强調上帝和靈魂之間的内在的,個人的關係。約瑟夫强调美在崇拜中的重要性,尼鲁斯懼怕美會成為偶像:(尼鲁斯堅持)修士不僅要在外部的貧困中獻身,還要在絕對的自我剝奪中獻身,他必須小心謹慎,以免獻身於他和上帝之間的美麗偶像或教會音樂。(在對美的質疑中,尼鲁斯展现出清教主義—幾乎是反偶像主義,這在俄羅斯的靈修中極其反常。)約瑟夫認識到共同崇拜和禮儀祷告的重要性: 人們能在自己的房間中祷告,但是房間中的祷告永遠不像教會中的祷告…………在教會裏,許多人的歌繫合在一起向神飛升,在合一之爱中只有一個思想和聲音…………塞拉芬在高處歡呼《三聖頌》 (Trisagion) ,大群人在底下歡唱同樣的讚美詩。天國與慶世在感思、喜悦和快樂中共度節日。3 3,引自, Meyendorff, (關於教會所起社會角色的爭論——十六世紀俄國教會財之執爭論) 另一方面,尼魯斯主要關心的不是禮儀禱告,而是神秘禱告:他在定居索拉之前,是阿索斯山上的修士,他對拜占庭的靜修士傳統有直接的認識。 俄羅斯教會正確地看到了約瑟夫和尼魯斯的教義中的優秀方面,將兩人都封為聖徒。兩人都繼承了聖塞吉鳥斯傳統的一部分,但只有一部分:修道主義的約瑟夫派形式和伏爾加派形式都為俄羅斯教會所需要,因為二者是互補的。雙方步入衝突的確令人哀傷,尼魯斯傳統受到很大的壓制:沒有非擁有者派,俄羅斯教會的靈性生活就成為單面的和不平衡的。約瑟夫派主張的教會和國家之間的緊密結合,他們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他們對崇拜的外在形式的投入——這些導致了下個世紀的麻煩。 阿甲按: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俄罗斯总体来说可能偏约瑟夫派「即拥有者派」多一点。 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在你去进入一个历史时段,时空的时候,你找到了这种张力,并且多数时候它没有办法解决,而是长期存在于历史长河中。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对于历史来说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历史不是一个静态的,而是充满活力、充满张力、充满动态,多元发展的过程。它不是铁块一块,不是一刀切,不是非黑即白的叙述结构。你越深入历史细节,越会意识到这一点。很多张力几百年前存在,到现在也存在,它没有办法解决。俄罗斯教会可能将来也始终会在教会的大公性与民族性之间摇摆,只不过是它可能在 一个历史时期更偏重于民族性,还是更偏重于大公性。从我目前的观察来看,俄罗斯教会现在可能更偏民族性一点。当然,我们从后面看到,这两个层面其实也是互补互需的。 在擁有者派和非擁有者派之間的爭論中,最有趣的參與者之一是希臘人聖馬克西姆(st Maximus the Greek, ?1470—1556) ,他是一位「桥梁人物」,他的漫長人生包含三個世界:文藝復興的意大利、阿索斯山和莫斯科。論出身他是希腊人,在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度過成年的早期階段,是米蘭多拉( Pico della Mirandola)等人文主義學者的朋友,他也在薩伏那洛拉( Savonarola)的影響下堕落,兩年後成為道明會修士。他在一五O四年回到希臘,成為阿索斯山修士,在一五一七年受沙皇邀請來到俄羅斯,把希臘人著作翻譯成斯拉夫文,修正被無数錯误歪曲的俄羅斯禱告書。同尼鲁斯一様他也投身於靜修士的理想中,一到達俄羅斯,他決定同非擁有者派共命運。 他同其餘的人一起遭受磨難,在監獄中被關押二十六年従一五二五年直到一五五一年。由於他提議修訂禱告書,所以在遭受攻撃時承受更大的痛苦,修訂工作中斷了,沒有完成。他極有學問,俄羅斯人本可從其中獲益良多,但由於他受監禁而被極大地浪費。在對自我剝奪和靈性貧困的要求方面,他和尼魯斯一様嚴格。他寫到:「如果你真的愛被釘十字的基督,你要做不為人知的陌生人,沒有國家,沒有姓名,在你的家人、熟人和朋友面前沉默;把你的一切都分給窮人,把你所有的舊習慣和你自己的意志都抛掉。4 4.引自 E Denissoft,《希服與東方的準則》 雖然擁有者派的勝利意味着教會與國家之間存在着緊密的聯盟,但是教會的獨立並未喪失殆盡。在伊凡雷帝的權力到達頂峰時,莫斯科的都主教聖菲利普( St Philip卒於1569年)敢於公開抗議沙皇的血腥和非正義,在舉行公共禮儀時當面指責他。伊凡將他關進牢裏,後來將他絞死。另一位尖鋭批評伊凡的人是被賜福者聖巴西爾( St Basil the Blessed)「聖愚」( Fool in Christ)(卒於1552年)。拜占庭的一種聖潔形式在中世紀的俄羅斯特別凸顯出來:「愚人」譴責所有智性天賦,一切形式的塵世智慧,自願背起瘋狂這座十字架,將自我剝奪和羞辱的理想發揮到極致,這是為了基督而些「愚人」通常發着有价值的社會作用:仅仅因為他們的愚,他們能夠以其他人不敢具有的坦率批評那些當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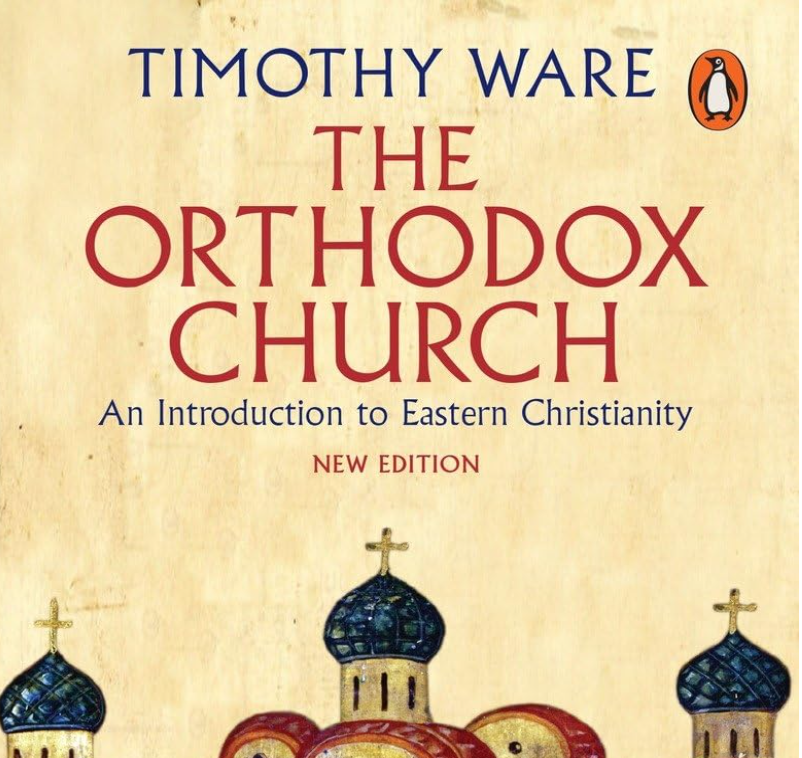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课系列第九课,黑暗时代——伊斯兰下的东正教。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九课:伊斯兰下的东正教》,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11月22日),讲稿由阿甲整理而成,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本讲稿由阿甲修订,很多内容参考这个中译本。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论》,中译田原(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若无特别说明,文字均是维尔主教的中译。若有阿甲的按语,则会写上:“阿甲按”三个字,并以引用符号标出。 油管订阅,下载音频和视频,请见这里 正文 第五章 伊斯兰下的东正教 第五章 伊斯蘭教徒統治下的教會 阿甲按:伊斯兰教下的教会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通过将基督教变成二等宗教,基督徒变成二等公民,繁重的赋税,买卖总主教,禁止传教,限制出版物等全方位的手段,将基督教变成一个少数群体,最终凡是伊斯兰下的基督教都可以说是黑暗时期,只能力图自保而已。并且还不时爆发专门针对基督徒的屠杀活动。可以说,伊斯兰对基督教的压制超过所有世俗政权对基督徒迫害和压制,因为后者的迫害和压制是有时间限制的,是时断时续的,但伊斯兰下的基督教是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压迫,这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希臘教會在我們的時代堅定不屈 ……儘管它受到土耳其人壓迫和蔑視,這個世界上的誘惑和快樂,同世界初始時就有的奇蹟和大能,有着同樣的説服力和確定性。了解和思考無知而貧窮的人們多麼堅定不移、勇敢果斷、簡單率直地保持他們的信仰,真的非常令人欽佩。 —菜科特爵士(Paul Rycaut) 《希臘和亞美尼亞教會現狀》(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Greek and Armenian Churches, 1679) 一、帝國內的帝國 「在十字架曾勝利地樹立了那麼久的地方看到新月到處升起,實在大背常理」,布朗尼(Edward Browne)在一六七七年這樣説,其時正值他以神父身份到達君士坦丁堡的英國大使館之後不久。對於希臘人來説,一四五三年必定也大背常理。因為在一千多年的時間裏,人們把拜占庭的基督教帝國當作上帝對世界天佑神意的一個永久性要素。現在,「受上帝保護的城市」已經論陷,希臘人處於異教徒的統治之下了。 這個轉變不容易,但是土耳其人使它的艱難少了一些,他們在對待他們的基督徒臣民時相當寬厚。十五世紀的穆斯林對待基督教遠比西方基督徒在宗教改革和十七世紀時的彼此互待更加寬容。伊斯蘭教認為《聖經》是一部聖書,耶穌基督是一位先知,所以在穆斯林的眼中,基督宗教在某些問題上有錯誤,但不是全然荒谬,基督徒是「聖書之民」,不應該僅在異教徒的層面上對待他們。按照穆斯林的教義,基督徒不應該遭受迫害,只要他們安靜地服從伊斯蘭教的權力,他們的信仰就不受干涉地繼續下去。 這些原則指引着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蘇丹默罕默德二世Mohammed II)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前,希臘人稱他為「反基督的先驅和第二位西拿基立(Sennacherib) 」(亞述國王、公元前七0五至六八一年在位,曾兩度侵犯猶大國,亦曾擊敗巴比伦。) ,"但是他們發現他的統治其實具有非常不同的特微。當默罕默德得知宗主教職位空缺時,他召來修士根那迪烏斯(Gennadius) ,讓他就任宗主教職位。根那迪烏斯(?1405—?1472)在當修士以前就以喬治·斯科拉里奥斯(George Scholarios)的名字聞名,是著述等身的作家和當時最重要的希臘神學家。他堅決反對羅馬教會,任命他為宗主教意味着佛羅倫薩聯合協定最終被拋棄。蘇丹故意選中一位具有反拉丁信念的人擔任宗主教,這無疑具有政治原因:根那迪烏斯成為宗主教,希臘人尋求獲得羅馬天主教力量秘密支持的可能性就減小了。 蘇丹親自委任宗主教,動用禮儀授予他教牧職位,恰如拜占庭獨裁者們以前的作為。這一舉動具有象徵性:征服者、伊斯蘭教的戰士默罕默德,也成為正教的保護者,接手了一度曾由基督徒皇帝施行的任務。因此基督徒在土耳其社會秩序內的確定地位得到保證,但是正如他們不久後發現的,這種地位必定是低級地位。伊斯蘭教徒統治下的基督教是二等宗教,它的擁護者是二等公民。他們繳納重税,穿着特殊服飾,不允許服役,禁止同穆斯林女子結婚。教會的傳教工作不被允許,使穆斯林轉信基督教信仰是犯罪。從物質的觀點來看,基督徒背教成為穆斯林的誘惑無處不在。直接的追害常常增強教會的力量,但是奥斯曼帝國的希臘人通常被剝奪了更加英勇地見證他們信仰的方式,相反卻要承受無情的社會壓力帶來的沮喪結果。 情况不止於此。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後,教會不得恢復君士坦丁皈依以前的狀態,這頗具悖論性,「歸凱撒的」現在較以前任何時候都同「歸上帝的」有更緊密的聯繫。因為穆斯林沒有在宗教和政治之間做出區分:在他們看來,如果基督教被視為一個獨立的宗教信仰,基督徒必須被組織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單位,一個帝國中的帝國。正教會因此既是世俗的也是宗教的機構:它變成「羅馬國家」(Rum Mille)。教會組織完全變成世俗管理的工具。主教變成政府官員,宗主教不但是希臘正教會的靈性首領,還是希臘國家的世俗首領——統治者(ethnarch)或政治首领(miller—bashi) 。這—情況在土耳其延續到一九二三年,在塞浦路斯延續到大主教馬卡里阿斯(Makarios)三世去世時(1977年) 。 這一政治(millet)體制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使得作為一個特殊單位的希臘國家有可能在外來統治下維持四個世紀。但是它給教會生活帶來兩個悲慘的結果。首先,它導致正教和民族主義悲哀地混淆在一起。希臘人的世俗生活和政治生活完全圍繞教會組織起來,他們幾乎不可能區分出教會和國家。普世的正教信仰不限於單個的人、文化或語言,但是對於土耳其帝國內的希臘人來説,「希臘文化」和正教不可避免地糾結在一起,其程度遠遠超過拜占庭帝國內的任何時期。這種混淆的結果一直延續到今天。 第二,教會的高級管理開始陷入腐敗和買賣聖職的可恥體系中。當主教們捲入世俗事務和政治事務時,他們堕落為野心和財務贪婪的犧牲品。每位新宗主教在就任前都需要獲得蘇丹的授權書,他不得不花重金獲取這份文件。宗主教的花費在他的主教轄區得到補償,他在教區勒索所有被委任聖職以前的主教們,主教們接下來勒索教區的神父,神父勒索他們的信徒。一切都是有償出售的:曾經適用於羅馬教廷的指責肯定也適用於土耳其人統治下的普世宗主教區。 當幾位候選人競爭宗主教職位時,土耳其人實際上把它賣給出價最高的人,他們很快注意到儘可能頻繁地更宗主教,以此增加售賣授權書的機會符合他們的財政利益。宗主教被撤職和復職的速度令人眼花繚亂。「在十五到二十世紀間的一百五十九位就職的宗主教中,土耳其人一百零五次將宗主教趕下台;退位有二十七次,常常是自願的;六位宗主教由於绞刑·毒藥或溺水而慘死;只有二十一位宗主教在位時自然死亡。」1同一個人有時上台四五次。時常還有幾位前宗主教在流放期間虎視眈眈地伺機重新掌權。宗主教極具不安全感,自然導致連绵不斷的陰謀出現在有望接替他的神聖會議都主教中,教會的领袖們常常分裂成殘酷敵對的派系。 七世紀居住在列凡特(Levant)的一個英國人寫道:「每個良善的基督徒都應該帶着悲傷去思考,帶着同情去目睹這個曾经辉煌的教會撕破她自己的腸腑,讓禿鷹和烏鴉,世界上野蛮而殘忍的動物吃掉它們。21B.kidd《东部基督教世界的教会)( The Churches of EasTern christendom 1927),页304 2.Sir PauI Rycaut《希腊和亞美尼教会的现状) 但是如果說君坦丁堡宗主教區遭受内部的衰敗,它的勢力則在外部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展。土耳其人把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視為其疆域内所有正教基督徒的領導者。其他宗主教區如亞歷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也都位於奧斯曼帝國,它們從理論上說是獨立的,但實際上處於從屬地位。同様受土耳其人控制的保加利亞教會和塞爾維亞教會,逐漸喪失了完全的獨立,到十八世紀中期時直接受普世宗主教控制。但是在十九世紀,隨着土耳其勢力的衰微,宗主教區的邊界收縮了。擺脱土耳其人控制的國家發現,繼續在教會事務上臣服於一個在土耳其首都居住並深深卷入土耳其政治體制的宗主教是不切實際的。宗主教千方百計地對之抵制,但每次最终都在必然性面前無可奈何。一系列民族教會脱離了宗主教區:希臘教會(一八三三年組建,一八五0年得到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認可) ;羅馬尼亞教會(一八六四年組建,一八八五年被承認) ;保加利亞教會(一八七一年重建,直到一九四五年才被承認) ;塞爾維亞教會(一八七九年恢復和被承認) 。宗主教區的縮小持續到二十世紀,這主要是由於戰爭,它在巴爾幹半島的成員數現在只是它在奥斯曼帝國政權興盛時期的一小部分。 土耳其人的占领給教會的知識生活帶來兩個相反的結果:它一方面是巨大的保守主義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一定程度的西化的原因。土耳其人統治下的正教發現自身處於守勢。最大的目標就是生存——在對更佳時日來臨的期待中維持事務運行。希臘人具有奇蹟般的韧性,堅持他們從拜占庭那裏承襲而來的基督教文明,但是幾乎沒有機會創造性地發展這一文明。他們常常滿足於重複已被確認的公式,對自己過去所繼承的立場墨守成規,這很好理解。希臘思想陷入僵化和硬化之中,這不得不令人遺憾,然而保守主義也有其自身優勢。希臘人確實在一個黑暗而艱難的時期,使正教傳統大體上未受損傷。受伊斯蘭教徒統治的正教徒以保羅講給提摩太的話為指引: 「你要保守所託付你的。」(提前6:20)他們最後選中更好的箴言了么? 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正教神學中,與保守主義相並行的還有另外一個相反的潮流:西方的滲透大潮。對於奥斯曼帝國統治下的正教徒來説,維持優秀的學術水準是困難的。想要獲得高級教育的希臘人不得不前往非正教世界,去意大利和德國,去巴黎,甚至是牛津。在土耳其時代的傑出希臘神學家之中,有少數人是自學的,但是絕大多數人在西方接受羅馬天主教或新教教師的培養。 這必然對他們解讀正教神學的方式產生影響。希臘學生必然會在西方閲讀教父們的著作,但是他們只熟悉他們的非正教徒教授們所尊敬的教父的著作。所以雖然阿索斯的修士們仍然閱讀格列高利·帕拉瑪的靈修著作,但是對於土耳其時代大多數博學的希臘神學家來説,他完全不為人知。優斯特拉提奧斯·阿根迪(Eustratios Argenti 卒於?1758年)是其時代中最有能力的希臘神學家,他的著作一次也沒有引用帕拉瑪,是個典型的例子。帕拉瑪的一部主要作品《保衛神聖靜修士的三段編》( The Triads in Defence of the Holy Hesychasts)直到一九五九年時還有大部分未被出版,這表現出希臘正教神學在過去四個世紀中的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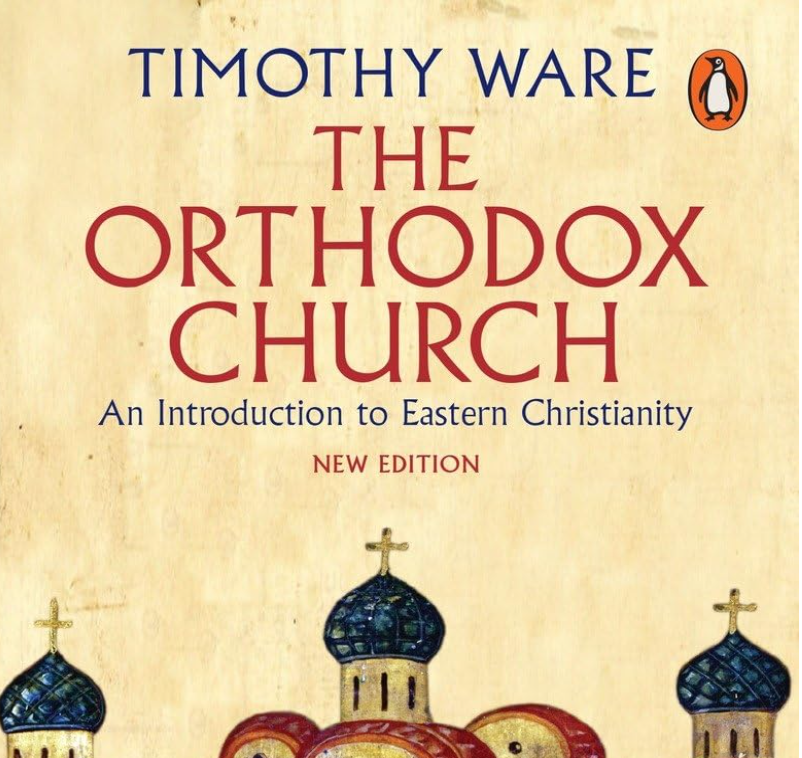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课系列第八课,斯拉夫的皈依。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八课:斯拉夫的皈依》,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10月11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本讲稿由阿甲修订,很多内容参考这个中译本。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论》,中译田原(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若无特别说明,文字均是维尔主教的中译。若有阿甲的按语,则会写上:“阿甲按”三个字,并以引用符号标出。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正文 第四章 斯拉夫人的皈依 阿甲按:维尔主教1-3章讲得比较简略,因为他的受众是西方教会,十字军东征之前,东西方还没有正式分裂,大家都还知根知底,所以就没有细说。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就转到斯拉夫民族。当今的斯拉夫民族在东正教起码占据半壁江山,是很有影响力的。下面我们就来讲讲他们的皈依史。 一、西里尔和美多迪鸟 对于君士坦丁堡来说,九世纪中期是一段密集传教活动的时期。拜占庭教会最终从反对破除圣像的长期斗争中解放出来,将力量转到皈依异教徒斯拉夫人上,斯拉夫人位于帝国北部和西北部的边境之外,包括莫拉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弗提乌斯是第一位在斯拉夫人中掀起大规模传教运动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他挑选出两兄弟执行这项任务,他们是来自塞萨洛尼卡的希腊人君士坦丁(Constantine, 826—869)和美多迪乌(?815—885) 。在正教会中,君士坦丁常常被称为西里尔,这是他成为修士时取的名字。他在早年时以「哲学家君士坦丁」闻名,在弗提乌斯的学生中最有才干,熟悉很多种语言,包括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甚至撒玛利亚方言。但是他和他兄弟的特殊才能是他们会斯拉夫语:他们在幼时学会了塞萨洛尼卡附近地区的斯拉夫方言,他们能够流利地使用这种语言。 西里尔和美多迪乌大约在八六0年短暂访问了居住在高加索北部地区的哈扎尔人(Khazars)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传教之旅。这次远征没有取得甚么永久结果,数年后哈扎尔人采纳了犹太教。兄弟两人的真正工作开始于八六三年,他们在那时赶赴莫拉维亚(大约相当于现代的捷克斯洛伐克) 。 他们的行程是应那裏的王子罗斯蒂斯拉夫(Rostislav)的请求,王子请求派遣能够使用自己语言布道和使用斯拉夫语进行礼拜活动的基督教传教士。斯拉夫语的礼拜需要斯拉夫文《圣经》和斯拉夫文礼拜手册。在兄弟两人前往莫拉维亚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着手这项浩大的翻译任务了。他们必须先创造出一套合适的斯拉夫字母表。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使用了自幼年时就熟悉的那种斯拉夫语形式,即塞萨洛尼卡附近的斯拉夫人说的马其顿(Macedonian)方言。马其顿斯拉夫人的方言以这种方式成为斯拉夫教会(的语言) ,它在今天仍然是俄罗斯和其他一些斯拉夫正教会使用的礼仪语言。 西里尔和美多迪鸟在离开拜占庭,前往未知的北部时随身携带了斯拉夫译本,人们不能高估它对正教未来的作用。在教会的传教历史上,如此重要的事情鲜有发生。斯拉夫基督徒在一开始就享受一项不为当时的西欧人享有的珍贵特权:他们使用自己能够理解的语言听讲福音和教会礼拜。不像西部的罗马教会坚持拉丁语,正教会在语言问题上从不僵化,它的标准政策是使用人们的语言做礼拜。 阿甲按:他们在去传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个翻译活动。可见,传教活动其实是伴随著翻译活动的,即翻译活动是传教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给斯拉夫民族传教就是一个例子,当时的斯拉夫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它们就造了字母表和语言体系,所以从骨子里「文字上」斯拉夫受东正教的影响就很深远。在中国也有个传教成功的例子,就是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掀起了一股翻译佛经的风潮,很多的这个贵族,士大夫整日无事,就开始研究佛经,玄学,老庄等。这些译作就从上往下在中国流传开来。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几乎达到巅峰。随后,安史之乱以后,民族情结兴起,就开始以宋明理学压制佛教。总体来说,佛教已经是中国文化这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究其原因,其早期的译经活动可谓功不可没。 就像在保加利亚一样,在莫拉维亚的希腊传教团很快也和在同一地区传教的日耳曼传教团发生了冲突。两个传教团不仅依赖不同的宗主教区,而且按照不同的原则工作。西里尔和美多迪鸟在礼拜中使用斯拉夫语,日耳曼人使用拉丁语;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朗诵原版信经,日耳曼人朗诵加入「和子」的信经。 阿甲按:可惜的是,据我所知,目前《金口约翰侍奉圣礼》尚未出现一个统一的、标准的中译本。我尚未听说哪位主教成立委员会去着手翻译侍奉圣礼。有个别正教信友翻译了日常礼仪文本以供正教徒使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站在教会的角度,礼仪文本的翻译是首当其冲的,其他一些现代圣人传记也于信徒灵性有益。我们《教父原文中译计划》更着重学术角度让大家了解这些东方教会传统,二者可谓相得益彰。 为了使自己的传教工作不受日耳曼人干涉,西里尔决定将传教工作置于教宗的直接保护之下。西里尔求助罗马的行动显示出,他没把弗提鸟斯和尼古拉之间的争吵太当回事,对于他来说,只要他能够继续在教会礼仪中使用斯拉夫语,东部和西部就仍然联合成一个教会,他依靠君士坦丁堡还是依靠罗马的问题,不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问题。兄弟俩在八六八年亲自赶到罗马,他们的请求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尼古拉一世在罗马的职任者哈德里安二世(Hadrian II)高兴地接受了请求,对希腊传教团给予全力支持,确认斯拉夫语为莫拉维亚的礼仪用语。他赞成兄弟俩的译本,把斯拉夫文的礼拜手册副本放在了城中主要教堂的圣坛上。 阿甲按:目前在基督教学术研究领域,天主教是最好的,无论是原始文献还是学者方面。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就藏有不少珍贵的教会史料。这里我们就看到最早的斯拉夫译本是在罗马。 西里尔在罗马逝世(869年) ,美多迪乌返回莫拉维亚。情况令人悲哀,日耳曼人置教宗的决定于不顾,尽一切可能的方式阻挠美多迪乌,甚至将他投入狱中,长达一年多时间。当美多迪乌在八八五年逝世时,日耳曼人把他的同伙驱逐出境,将他们中的许多人贩卖为奴。斯拉夫语传教团的蹤影在莫拉维亚继续留存了两个多世纪,但是最终被彻底根除;具有拉丁文化和拉丁语言(当然还有「和子」)的西方形式的基督教开始成为普遍。在莫拉维亚建立斯拉夫国家教会的尝试一无所得。西里尔和美多迪乌的工作似乎以失败终结。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兄弟两人未曾亲自前去布道的其他国家从他们的工作中获益,最突出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如我们前面所见,保加利亚的可汗鲍里斯曾经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犹豫不定,但最终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管理。虽然在保加利亚的拜占庭传教士缺乏西里尔和美多迪乌的视野,起初使用希腊语做教会礼拜用语,对于普通的保加利亚人来说,希腊语像拉丁语一样无法理解。但是当美多迪乌的学生们被赶出莫拉维亚以后,他们自然地转入保加利亚,将莫拉维亚传教团采取的原则引入到这裏。希腊语被斯拉夫语取代了,呈现给保加利亚人的是他们能够吸收的,具有斯拉夫形式的拜占庭基督教文化。保加利亚教会迅速成长。大约在九二六年,正逢沙皇西蒙大帝(Symeon the Great893—927年在位)统治时期,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宗主教区建立起来,在九二七年得到了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承认。鲍里斯建立自己独立教会的梦想,在他死后半个世纪内变为现实。保加利亚是斯拉夫人的第一个国家教会。 拜占庭传教团也进入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在九世纪后半期,大约在八六七至八七四年间接受了基督教。塞尔维亚也位于东部和西部基督教世界的分割线上,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犹豫不定后,它遵循了保加利亚而非莫拉维亚的范例,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管理。在这裏,斯拉夫语礼拜手册被引入,一个斯拉夫一拜占庭文化成长起来。塞尔维亚教会在圣萨瓦(St Sava, 1176—1235)的领导下获得了部分的独立,圣萨瓦是最伟大的塞尔维亚族圣徒,他于一二一九年在尼西亚被祝圣为塞尔维亚大主教。塞尔维亚宗主教区在一三四六年建立,在一三七五年得到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承认。 俄罗斯人的皈依在间接上也可归于西里尔和美多迪乌的工作,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谈。来自塞萨洛尼卡的两位希腊人有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作其「灵性孩子」,他们完全配得上「斯拉夫人的使徒」的称号。 巴尔干人的另一个正教国家罗马尼亚,具有更加复杂的历史。罗马尼亚人虽然受到他们的斯拉夫人邻居的影响,但在语言和种族方面主要是拉丁的。相当于现代罗马尼亚一部分的达西亚(Dacia) ,在一0六至二七一年期间是罗马的一个行省,但是此时建立起来的基督教团体似乎在罗马人撤退以后消失了。保加利亚人在九世纪末或十世纪初时,显然使部分罗马尼亚人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瓦拉 几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直到十四世纪时才完全皈依基督教。 那些认为正教是完全「东部的」,其有希腊和斯拉夫特征的人,不应该忽略罗马尼亚教会的事实,它在今天是第二大正教会,主要具有拉丁的民族身份。拜占庭授予斯拉夫人两件礼物:一套完整清晰的基督教教义体系和一个充分发展的基督教文明。当斯拉夫人在九世纪开始皈依时,教义争端的重大时期和七次大公会议时期已经结束了。信仰的主要轮廓——圣三一和道成肉身教义——已经被制定出来,具有确定形式的信仰传到斯拉夫人中。也许这是斯拉夫教会之所以很少造就出原创性神学家的原因,而出现在斯拉夫地区的宗教争端通常都不是教义性质的。但是对于圣三一和道成肉身的信仰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伴随其传播的是一整套基督教文化和文明,这也是希腊传教士从拜占庭随身带来的。斯拉夫人同时被基督教化和被开化。 阿甲按:斯拉夫民族最大的贡献不来自于教义,神学层面,有原创性的不多,而在于其践行的精神和圣人传统。因为传给他们的时候,这些教义,神学层面的东西已经通过七次大公会议讲通了。但斯拉夫民族有自己的风格,比如他们的语言,建筑,服饰等。 希腊人不是以陌生的而是以斯拉夫的外衣传播这一信仰和文明(西里尔和美多迪鸟的译本在这裏具有首要意义) ,斯拉夫人能把他们借自于拜占庭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如果拜占庭文化和正教信仰起初主要限定于统治阶级,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它在整体上变为斯拉夫人日常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创造独立的国家教会体系,教会和民众的联系甚至更加紧密了。 正教和民众生活,特别是和国家教会体系的紧密一体化,必定会带来不幸的结果。因为教会和国家的联系是如此紧密,正教斯拉夫人常常将两者混淆,使教会服务于国家政治目的。他们有时倾向于首先视其信仰为是塞尔维亚的、俄罗斯的或保加利亚的,忘记它首先是正教和公教的,这也是希腊人在现代受到的诱惑。民族主义在上一千年中已经成为正教的祸根。而教会和人民的联合在最后被证明具有巨大的助益。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实则成为全体人民的宗教,最佳意义上的大众宗教。 阿甲按:这里维尔主教毫不避讳地批评东正教内部民族主义的倾向。比如,这种观点倾向与这样说:东正教只属于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必须属于东正教,两者不能分开。人加入东正教就必须先变成俄罗斯人,学习他们的一切风俗「语言,服饰,舞蹈,食物等等等」,甚至说,如果你没有俄罗斯血统,你不配受洗等等。或者说,只有俄罗斯的东正教是最高级,最正统的,其他的都偏离了真道。这种言论就是我所说的宗教与民族混同主义,是异端教导。 二、俄罗斯人的洗礼:基辅时代(988-1237) 阿甲按:988-1237是俄罗斯消化吸收希腊东正教传统的时间,历经两百多年。如今东正教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要消化吸收它,没有两三百的持续过程是不可能。比如,佛教在中国扎根,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几百年的译经活动所致。传统教会不像麦当劳,到哪里都一样,食物也没有太多变化。传统教会到一个地方会有自己的风味,这个过程没有几百年的消化和吸收是不可能的。 弗提斯也计划使俄罗斯的斯拉夫人皈依。他大约在八六四年派遣一位主教前往俄罗斯,但是这第一个基督教根据地被奥雷格(Oleg)刬除了,奥雷格于八七八年在基辅(俄罗斯当时的主要城市)掌权。但是,俄罗斯继续经历拜占庭、保加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基督教的继续渗透,基辅在九四五年建立了一个教会·俄罗斯公主奥尔佳(Olga)在九五五年成为基督徒,但是她的儿子斯维亚托斯列夫(Svyatoslav)拒绝效仿她,说如果他接受基督教洗礼,他的随从会嘲笑他。 可是,奥尔佳的孙子弗拉基米尔( Vladimir,980-1015年在位)大约在九八八年皈依了基督教,娶了拜占庭皇帝的姐妹安娜(Anna)。正教成为俄罗斯的国教,一直持续到一九一七年。 阿甲按:这种联姻很难说一定是宗教性的,可能更多的是政治性的。比如说,古代隋唐时期,这种把公主嫁到西域的少数民族或者西域民族把他们的王子放到长安的王宫里做质子就是防止打仗。 弗拉基米尔热切地希望在他的国土上展开基督教化:神父、 圣物、圣器、圣像被引入;大量的洗礼在河边举行;教会法庭被建立,教会称呼被确立。有着银首和金胡子的巨大的佩伦(Perun)神偶像,被从基辅的山顶上可耻地扯下来。「天使的号角声和福音的雷声响彻所有城镇。朝神飞升的香烟圣化了空气。山上矗立起修道院。男人和女人,年幼和年长的人,所有人都涌入神圣的教堂。」1希拉里安都主教在六十年后这样描述这一事件,他的描述无疑具有一定的理想化;因为基辅的俄罗斯人没有全部立即皈依基督教,教会最初主要限定于城市中,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以前,大多数农民都是异教徒。 阿甲按:我觉得这个评论是中肯的。多数情况下,一个宗教在一个国家发展,它的趋势就是从自上而下的。大概要经历两三百 年,几代人以后,慢慢地渗透到下面去。其实这也是佛教发展的一个过程,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力发展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一些西域的少数民族,一些王宫贵族大力地提倡佛教,出资建佛寺,然后佛教就开始在普通老百姓中变得流行起来。我相信俄罗斯的教会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它可能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时间。首先是王宫贵族,然后就是上行下效。即便执政者的资本,力度和推广度是极大的,推广到民间仍需要至少两三百年的时间。 弗拉基米尔与施舍者约翰一样强调基督教的社会内涵。每当他同他的朝臣享受盛宴时,他就给穷人和病人分发食物;在欧洲地中海地区,没有其他地方像十世纪的基辅这样拥有如此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服务」。基辅俄罗斯的其他统治者们都以弗拉基米尔为榜样。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Vladimir Monomachos1113-1125年在位)在给其子的《遗言(Testament)中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忘记穷人,尽你之所能支持他们。向孤儿施舍,保护寡妇,不允许强大者毁掉别人。」2弗拉基米尔也深知基督教的仁慈律法,当他将拜占庭的法典引入基辅时,他坚持缓和其比较野蛮和残忍的特性。基辅俄罗斯没有死刑,断肢,拷打,很少 使用肉体刑罚。 阿甲按:基督教的社会慈惠事工,社会属性是基因里的。因为圣经说,上帝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丈夫、穷人的守护 者。这些话在教父眼中都不是虚言,因此四世纪的巴西尔建立了福利院,金口约翰谴责富人吝啬,批评他们奢靡的生活。近代中国也深受基督教这种社会慈惠精神的影响,比如来华的宣教士建立学校,医院,养老院,孤儿院,这些都是明证。 同样的温顺可见于弗拉基米尔的两个儿子鲍里斯和格列波(Gleb)的故事中。弗拉基米尔在一0一五年一逝世,他们的长兄斯维亚托波尔克(Svyatopolk)试图攫取公国的权力。他们真正遵守福音的诫命,没有进行抵抗,虽然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进行抗,两人反倒被斯维亚托波尔克的密使谋杀了。如果要流血,鲍里斯和格列波宁可让自己流血。虽然他们不是为信仰而殉道,而是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 是他们被封为圣徒,被授予「受难者(Passion Bearers)的特别称号:人们从他们无辜而自愿的受难中感受到他们分享了基督的受难。俄罗斯人始终极为看重受难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地位。 阿甲按:上面提到东正教的国教特点。其实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圣人传统。如果政治的支持是外在的,那么圣人传统则是潜移默化,内在的,它感化的不只是一代人,是好几代人,这些圣人以及传记塑造整个民族的性格。 因此,俄罗斯的圣人传记是值得好好学习效法的,因为他们效法基督。这当然也影响了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有很深的忏悔和反思在这些作品中,这些都是因为圣人传统的影响。而我们中国的文学作品很少有这些东西,多是像鲁迅说的,仁义道德只不过是吃人的借口,没有绝对的正义,一切都不过是成王败寇的托词罢了。 如同在拜占庭和地中海西部一样,修道院在基辅俄罗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辅最有影响力的修道院要数名为「佩切尔斯基拉瓦」(Pethersky Lavra)的洞穴修道院。它最初是一所半隐修修会。创建者是曾经在阿索斯山上生活的俄斯人圣安东尼,继任者圣狄奥多西(卒于1074年)重组修道院,仿照君士坦丁堡的斯托迪奥修道院,引入了完全的团体生活。同弗拉基米尔一样,狄奥多西也知道基督教的社会重要性,他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运用它们,使自己同穷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很像西部的阿西西的圣方济(St Francis of Assisi)的作为。鲍里斯和格列波追随基督献祭牺牲;狄奥多西追随基督过贫穷的生活和自愿「虚己」(self–emptying, kenosis)。 他出身高贵,但在幼年时期就选择穿粗陋的补丁衣服,和奴隶们一起在田间劳作。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变成穷人,屈尊使自己成为榜样,所以我们应当以他的名义使自己卑微。他为了拯救我们而遭受辱駡、唾弃和鞭打。那么,我们为了获得基督而遭受困苦是多么地公正。」即使当选为修道院长以后,他也穿着最简陋的衣服,拒绝一切外在的权威标记。但是在同时,他也是贵族和王子们所尊敬的朋友和顾问。 虚己的谦卑思想同様也可见于其他人,例如弗拉基米尔的路加主教(Luke of Vladimir ,卒于1185年)用《弗拉基米尔编年史》(Vladimir Chronicle)的话来说,他「自身承受基督之辱,没有尘世之城,而在寻觅未来之城」。这种理想常常存在于俄罗斯民间傅说中,也存在于诸如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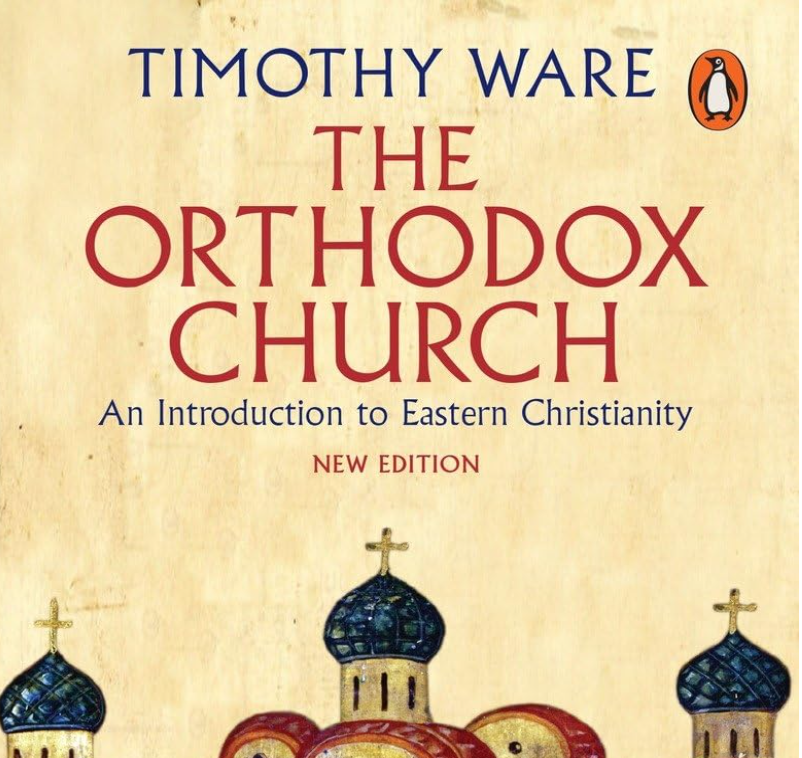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课系列第六至七课,东西分开篇。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六课》,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9月6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本讲稿由阿甲修订,很多内容参考这个中译本。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论》,中译田原(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若无特别说明,文字均是维尔主教的中译。若有阿甲的按语,则会写上:“阿甲按”三个字,并以引用符号标出。此篇以体现维尔主教著作为主,若要听阿甲的评论,请听讲座。 正文 第三章 拜占庭之二 :大分裂 我们是不变的;我们仍然是8世纪时的我们……多么希望你们能够同意再次成为你们曾经之所是,我们那时在信仰和团契中合一!——科米亚科夫(Alexis Khomiakov) (一) 东方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疏远 在1054年的一个夏日午后,当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教堂正要开始进行事奉礼仪的时候,枢机主教洪波特(Cardinal Humbert)和另外两位教廷使节走进圣堂中。他们不是来祈祷的。他们把一张逐出教会的教宗诏书放到圣坛上,又走了出去。当枢机主教走过西门时,他抖掉脚上的灰尘,说着:“让上帝去看和裁决吧!",一位执事跑出去追他,这位执事非常悲痛,乞求他收回教宗诏书。洪波特拒绝了;诏书被扔到大街上。 按照惯例,这一事件标志着正教东方与拉丁西方之间大分裂的开始。但是现在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大分裂事件的开始日期不能精确地被确定。大分裂的来临是渐进的,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的结果,它在11世纪开始之前发生,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仍未结束。 在这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许多不同的影响力量发挥了作用。大分裂受到文化、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作用,可是其基本原因并非是世俗的,而是神学上的。东西方最后是关于教义的问题进行争吵,特别是在关于教宗主张与「和子」(filioque)这两个问题上。但是我们在更详细地考察双方的主要区别之前,在考虑大分裂的实际进程之前,必须介绍更广阔的背景。在东西方之间发生公开而正式的大分裂很久以前,双方就开始互为陌生人;在试图理解基督教世界的共融如何与为何分裂之前,我们必须从这个渐行渐远的事件的发展开始入手。 当圣保罗和其他的宗徒环绕着地中海世界旅行的时候,他们是在罗马帝国这个有着紧密的政治和文化联系的统一体内行走。这个帝国包含许多不同的民族团体,他们常常具有各自的语言和方言。但是所有这些团体都被同一个皇帝统治,博大的希腊文明为帝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所享有的;帝国各处的人们几乎都能听懂希腊语或拉丁语,许多人能讲两种语言。这些事实对早期教会进行福传工作有极大的裨益。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地中海世界的统一逐渐消失了。首先消失的是政治统一体。自从3世纪末期以来,帝国虽然在理论上仍然是统一的,但是分裂成为东方和西方两部分,每部分都有各自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通过在东方建立帝国的第二都城,与意大利的旧罗马相并列的都城,推进了这一分裂过程。 在5世纪开始时,出现了蛮族的入侵,除了意大利以外,西方被蛮族首领瓜分殆尽,意大利的大片领土在较长的时期内仍保留在帝国内。拜占庭人从未忘记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统治时的罗马理想,仍然认为他们的帝国在理论上是统一的;但是查士丁尼是认真地尝试在理论和现实之间架设桥梁的最后一位皇帝,他不久就放弃在西方的征战。蛮族的入侵摧毁了说希腊语的东方和讲拉丁语的西方的政治统一体,并且永远都未恢复起来。 在6世纪晚期和7世纪,阿瓦人(Avar)和斯拉夫人入侵巴尔干半岛,这加深了东方和西方的互相孤立,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曾充当桥梁的伊利里库姆(Illyricum)成了拜占庭和拉丁世界之间的屏障。伊斯兰教的兴起继续使分离延续,地中海一度被罗马人称为mare nostrum,我们的海,现在则主要落入了阿拉伯人之手、地中海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文化和经济接触从未完全消失,但是变得愈加困难。 反圣像争论对于拜占庭和西方之间的分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教宗坚定地支持偶像崇拜论的立场,因此他们发现自己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同君士坦丁堡的反圣像的皇帝和宗主教失去了共契。教宗斯蒂芬(Stephen)受到拜占庭的孤立而需要帮助,他在754年向北方求助,访问了法兰克人的统治者佩金(Pepin)。就罗马教廷而言,这标志着决定性的方向转换的第一步。迄今为止,罗马在很多方面仍然是拜占庭世界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它逐渐地接受法兰克人的影响,虽然这一重新转向的结果直到11世纪中期才变得完全明朗。 在教宗斯蒂芬访问佩金半个世纪以后,一件更加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了。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宗利奥三世(Leo Ⅲ)为法兰克人的皇帝,查理大帝加冕称帝。查理曼曾经寻求拜占庭统治者的认可,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拜占庭人仍然坚持帝国统一的原则,认为查理曼是入侵者,教宗为他举行的加冕仪式是分裂帝国的举动。神圣罗马帝国在西方的创建,并没有使欧洲变得更加凝聚,只是使东方和西方的疏远较以往更为严重。 文化统一体继续保留着,但是却采取了一种非常微弱的形式。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有教养的人仍然生活在古典的传统之中,这个传统被教会所接管并被教会据为己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开始以日渐相异的方式解释这一传统。语言的问题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受教育的人说双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到了450年,西欧很少有人能读懂希腊文,在600年以后虽然拜占庭仍然自称是罗马帝国,但是拜占庭人很少讲罗马人的语言——拉丁语。9世纪君士坦丁堡最伟大的学者圣大弗提乌斯(Photius)不能阅读拉丁语,在864年,拜占庭的一位"罗马"皇帝麦克三世(Micheal Ⅲ)甚至称维吉尔(Virgil)的写作用语为"蛮族和赛斯人(Scythic)的语言”。如果只懂希腊文或者拉丁文的人士想要阅读对方语言的著作,就只能阅读翻译本,通常他们不在这方面花费力气:赛鲁斯(Psellus)是11世纪时的一位博学的希腊学者,他的拉丁文献知识却是如此贫瘠,以致于把凯撒(Caesar)混淆为西塞罗 (Cicero)。因为他们不再使用相同的文献,也不再阅读相同的书籍,讲希腊语的东方和拉丁语的西方渐行渐远。 查理曼宫廷的文化复兴自一开始就打上了强烈的反希腊的偏见的印记,这是一个不详但却重要的先例。欧洲在4世纪时就有一个基督教文明,在13世纪时有两个基督教文明。也许在查理曼统治时期,两个文明的分裂第一次变得清晰醒目。拜占庭人在他们自己的思想世界里徜徉,没有在半路上遇见西方。在9世纪和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拜占庭人也常常不能认真对待西方的知识。他们把所有法兰克人都当做蛮族予以遣散。 这些政治和文化因素不能不影响教会生活,使教会更难以维持宗教统一。文化和政治上的疏远容易导致教会争端,从查理曼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拜占庭皇帝拒绝承认查理曼的政治地位,查理曼被指控为脱离拜占庭教会的异端,他很快对这一指控做出报复:他指责希腊人在信经中不使用「和子句」(我们稍后将详细论及此点),他拒绝接受第七次大公会议的决定。真实情况是,查理曼通过一个严重歪曲原意的错误译本才知道这些决定,但是无论如何他的观点看上去都是半反偶像的。 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政治环境使教会具有不同的外在形式,所以人们渐渐以互相冲突的方式理解教会的教令。自一开始,东方和西方的着重点就有一定的差异。在东方,许多教会的基础都可以追溯至宗徒,所有主教都有着强烈的平等意识,教会具有法团和会议的特性。东方认为教宗是教会的首席主教,但是把他视为平等者中的首席。另一方面,在西方只有一个大主教教区——罗马——声称具有唯一宗徒传承的基础,罗马因此被视作是宗徒教区。虽然西方接受了大公会议的决定,但是自己却不在会议中发挥积极作用,与其说教会被视为法团,不如说是被视为君主国——教宗的君主国。 这个最初的观点分歧由于政治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尖锐。蛮族的入侵,随后帝国在西方的瓦解自然极大地强化了西方教会的专治结构。在东方,有一个强大的世俗首领——皇帝,支持文明的秩序并实施法律。在西方,当蛮族到来后,只有许多战争首领,所有首领或多或少都是篡位者。能够担当统一体中心的,能够在西欧的灵性和政治生活中担当连续而稳定元素的,主要是罗马教廷。借助环境的力量,教宗担任的角色是希腊宗主教不曾担当的,他不但向教会中的下级还向世俗统治者发布命令。西方教会的集权化逐渐发展,达到了东方四个宗主教区(可能出了埃及外)闻所未闻的程度。西方实行君主制,东方实行共同掌权制(collegiality) 蛮族入侵给教会生活带来的影响还不止于此。拜占庭有许多有教养的平信徒对神学有积极的兴趣。“平信徒神学家"始终是被正教接受的人物。一些最博学的拜占庭宗主教在接受宗主教职任命以前都是平信徒,例如圣大弗提乌斯(Photius the Great)。但是在西方,教会为其神职人员提供的教育是黑暗时代中唯一能够存活的有效教育。神学变成神父们的保留项目,因为大多数平信徒甚至不能阅读,遑论理解神学讨论的专业术语。正教虽然赋予主教特殊的教育职责,但从未闻知神职人员与平信徒之间的差距竟如此显著,这种差别出现在西方中世纪时期。 由于缺乏共同语言,东方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同对方的交流不再容易,每一方都不在能够阅读另一方的文字,误解更容易出现了。共享的"论域"逐渐消失了。 东方和西方变得互相陌生,双方都从中受难。早期教会虽然有多重神学学派,但却有统一的信仰。希腊人和拉丁人自一开始就在各自的道路上接近基督教的神秘。下述说法有过于简单化的危险:拉丁人的进路更具实践性,希腊人的进路更富冥想性;拉丁人的思想受到法律思想和罗马法观念的影响,而希腊人则是在礼仪敬拜的背景下,依照圣礼理解神学。在思考神圣三位一体时,拉丁人从一个神性开始,希腊人从三个位格开始;在思考十字架受难时,拉丁人首先想到基督是受难者,希腊人则认为基督是胜利者;拉丁人更多地讨论救赎,希腊人喜欢讨论圣化;等等。如同东方的安提阿学派和亚历山大学派一样,这两个不同的进路本身也不是互相冲突的;每个都是另一个的补充,每个都在完整的公教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双方现在变得互相陌生——没有政治上的统一,没有共同的语言,只有文化上的些微统一——每一方都面临着孤立地遵循各自进路和走向极端的危险,忘记了另一方观点的价值。 我们已经说到东方和西方具有不同的教义进路,但是在「教宗首席权」和「和子句」这两点教义上,双方却不再互补,而是进入了直接的冲突之中。我们再前述段落中提到过的因素,足以对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形成沉重的压力。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东西方之间或许仍然维持着统一。我们现在必须探讨这两个问题。完全的分歧直道9世纪中期才首次正式公开,但是这两个教义分歧的起源却相当早。 当我们讲到东方和西方具有不同的政治环境时,已经提到过教宗首席权,我们已经看到蛮族的入侵是如何强化了西方教会的集权制和君主制结构。现在,只要教宗在西方要求具有绝对的权力,拜占庭就不会提出反对。只要教宗的权力不干涉东方,拜占庭人就不介意西方教会是否集权化。然而,教宗相信他对西方和东方都具有直接的管理权,只要他试图在东方宗主教区运用这项权力,麻烦必定出现。希腊人授予教宗以最高的荣誉,而非教宗想当然的普世至尊权。教宗认为绝对无谬误性是他自己的特权,希腊人认为信仰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不为教宗独有,而为代表教会全体主教的会议所有。我们有了两种关于教会可见组织的不同观念。 12世纪的一位作家尼塞塔斯(Nicetas)是尼科米迪亚(Nicomedia)的枢机主教,他的一段话绝好地表达出正教对于教宗首席权的态度: ‘我最亲爱的兄弟,我们不否认罗马教会在五个姐妹宗主教区中居于首位,我们承认她在大公会议中享有位居最尊贵坐席的权利。但是她自己的行为却使她同我们相分离,她骄傲地呈现出本不属于其职权的君主制……她不同我们商议甚至不知会我们,就对我们发出命令,我们怎能接受这样的命令?坐在高耸的荣耀王座里的教宗,如果想对我们大发雷霆,在高处把命令掷给我们,如果他不同我们商量而是肆意评判我们,甚至想要统治我们和我们的教会,这是什么样的手足情谊,他又是如何为人父母的呢?有了这样的教会,我们就会是他的奴隶而非儿子,罗马教区不会是儿子们的虔诚母亲,而是奴隶们铁石心肠的奴隶主和飞扬跋扈的情妇。’——《东部的分裂》(The Eastern Schism),S.Runciman 当整个问题公开时,12世纪时的正教徒有了如上的感受。在前几个世纪中,希腊人对待教宗首席权的态度基本相同,但态度尚未被争端所激化。在850年以前,罗马和东方在教宗首席权的问题上避免公开冲突,但是观点分歧并没有由于部分地掩饰而得到缓和。 第二个大难题是「和子句」。《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中关于圣灵的词语引起了这场争论。信经最初写道:“我相信……圣灵、主、生命的赐予者,祂源出于父,祂同父和子一道被崇拜和被荣耀。“迄今为止,东方一直原封不动地引述这个最初的表述。但是西方另加了一句"和源出于子”(拉丁文Filioque),所以信经现在的写法是"祂源出于父和子” 不清楚这个附加词第一次在何时何地出现,但它似乎源于西班牙,是为了反对阿里乌主义(Arianism)。如果不是更早,就在第三次托莱多(Toledo)宗教会议(589年)上,西班牙教会加入了「和子」。这一附加词从西班牙开始传播到法兰西,然后传播到德国,在那里受到查理曼的欢迎,被法兰克福的半反偶像会议(semi-Iconoclast)(794年)所采用。查理曼宫廷的作家们首次使「和子」成为争议问题,希腊人由于引述最初的信经而被指控为异端。但是罗马采取了典型的保守主义立场,在11世纪开始以前一直使用没有「和子句」的信经。808年教宗良利奥三世在一封写给查理曼的信中说,虽然他本人相信「和子句」在信理上是合理的,但是他认为篡改信经的字句是错误的。利奥三世有意让人把没有「和子句」的信经刻在银质铭牌上,悬挂在圣彼得大殿里。此时的罗马在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之间充当调停人的角色。 希腊人直道850年才开始非常重视「和子句」,但是一旦他们重视起来,他们的反映是尖锐苛刻的。正教反对(现在仍然反对)给信经添加附加词的理由有两个。首先,信经是整个教会的共同财产,只有经过大公会议的同意,才能对信经做出修改。西方没有同东方商议就修改信经,(就像科米亚科夫所说)犯了道德上的弑兄之罪,是违反教会统一之罪。其次,大多数正教徒相信「和子句」在信理上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圣灵只源出于圣父,如果说祂也源出于圣子就是异端。可是,一些正教徒认为「和子」本身不是异端观点,可以真正作为一种神学观点——而非教义——而被采纳,条件是它能够得到正确的解释。但即便是这些采取更温和立场的人仍然认为「和子」是没有经过授权的附加词。 除了「教宗首席权」和「和子句」这两个主要问题,还有教会崇拜和纪律等次要问题引发东西方之间的争论,希腊人允许神职人员结婚,拉丁人坚持神父过独身生活;双方有不同的斋戒规则;希腊人在圣体血圣事中使用发酵饼,拉丁人使用未经发酵的饼或"无酵饼”。 东方和西方在850年左右时仍然有完全的共契,仍然形成统一的教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分隔共同导致疏远日益增长,但此时没发生公开的分裂。双方对于教宗权柄有不同的理解,使用不同的方式引述信经,但这些问题尚未完全公开。 但是在1190年,安提阿宗主教和伟大的教会法权威西奥多.巴尔萨蒙(Theodore Balsamon)在看待这些问题时,采取了极为不同的观点: ‘数年以来(他没说多少年),西方教会同其他四个宗主教区之间的灵性联系已经隔断了,已经同正教相疏远……只有拉丁人首先宣布放弃那些使他们同我们相隔断的教义和习俗,并受制于教会法规,(他们)才能恢复同正教的共契和联合。’ 《东部的分裂》 在巴尔萨蒙的眼中,共契被打破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分裂是确定的。双方不再构成一个可见的教会。 在从疏远到分裂的变迁中,有四件事的意义特别重要: 圣大弗提乌斯和教宗尼古拉一世(Nicolas Ⅰ)之间的争吵(通常被称为"弗提乌斯分裂");1009年的折合书(Diptychs)事件;1053至1054年的和解尝试及其灾难性的结果;十字军东征。 (二) 从疏远到分裂:858年至1204年 在狄奥多拉(Theodora)统治时的圣像运动胜利以后15年,也就是858年,一位新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弗提乌斯被任命,正教会称其为伟大的圣弗提乌斯。他被视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中最杰出的思想家,最卓越的政治家和最娴熟的外交家"—《拜占庭国家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在他就任宗主教后不久,就卷入了一场同教宗尼古拉一世(Nicolas Ⅰ)的争论中。上一位宗主教圣伊格纳修(St.Ignatius)遭到皇帝的流放,在流放期间迫于压力而辞职。圣伊格纳修的支持者们拒绝承认辞呈是合法的,认为圣弗提乌斯是篡位者。当圣弗提乌斯给教宗写信宣布自己的就任时,尼古拉决定在承认圣弗提乌斯以前,要进一步观察新宗主教和伊格纳修追随派之间的斗争。 因此在861年,他派使节出访君士坦丁堡,圣弗提乌斯不想发起同教宗的争论。他以大礼对待使节,邀请他们在君士坦丁堡主持一场会议,旨在解决圣伊格纳修和自己之间问题的会议。使节们和其余的会议成员一致决定圣弗提乌斯是合法的宗主教。但是当使节们回到罗马以后,尼古拉宣布他们越出了他们的权限,他推翻了他们的决定。然后他亲自在罗马继续重判这个问题:他在863年主持的一场会议中认定圣伊格纳修是合法宗主教,宣布免除圣弗提乌斯的一切教牧尊严。拜占庭人没有注意到这项谴责,没有回复教宗的信件。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裂痕公开出现了。 这场争论显然涉及教宗权柄。尼古拉是一位伟大的改革派教宗,得意地认为他的主教辖区享有诸多特权,他为了建立超越所有主教的绝对权力,在西方着力甚多。但是他相信这种绝对权力也应该扩展到东方,他在865年写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教宗被赋予了"超出全世界,即超出一切教会"的权威。这恰恰是拜占庭人不准备承认的。 面对圣弗提乌斯和圣伊格纳修的争斗,尼古拉认为他看到了一个实现其普世管理权的绝佳机会,他要使双方都承认他的裁决。但是他意识到圣弗提乌斯已经自愿的接受了教廷使节的调查,这个行动不意味着承认教宗的至尊地位。这(还有其他原因)是尼古拉之所以废除使节的决定的原因。 对于拜占庭人来说,他们愿意向罗马上诉,但这只是在萨迪卡(Sardica)宗教会议(343年)的第三条教规规定的特殊情况下。这条教规规定,如果主教被定罪,他能够向罗马和教宗上诉;如果教宗理解诉讼的原因,就能命令重审(案件);然而,进行重审的不是罗马的教宗本人,而是被定罪主教的临近省区的主教们。教宗尼古拉推翻了他的使节们的决定并要求由他本人在罗马重新审定,拜占庭人认为这违反了教规的规定。他们认为他的行为是没有根据的和不合教规的,干涉了其他宗主教区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