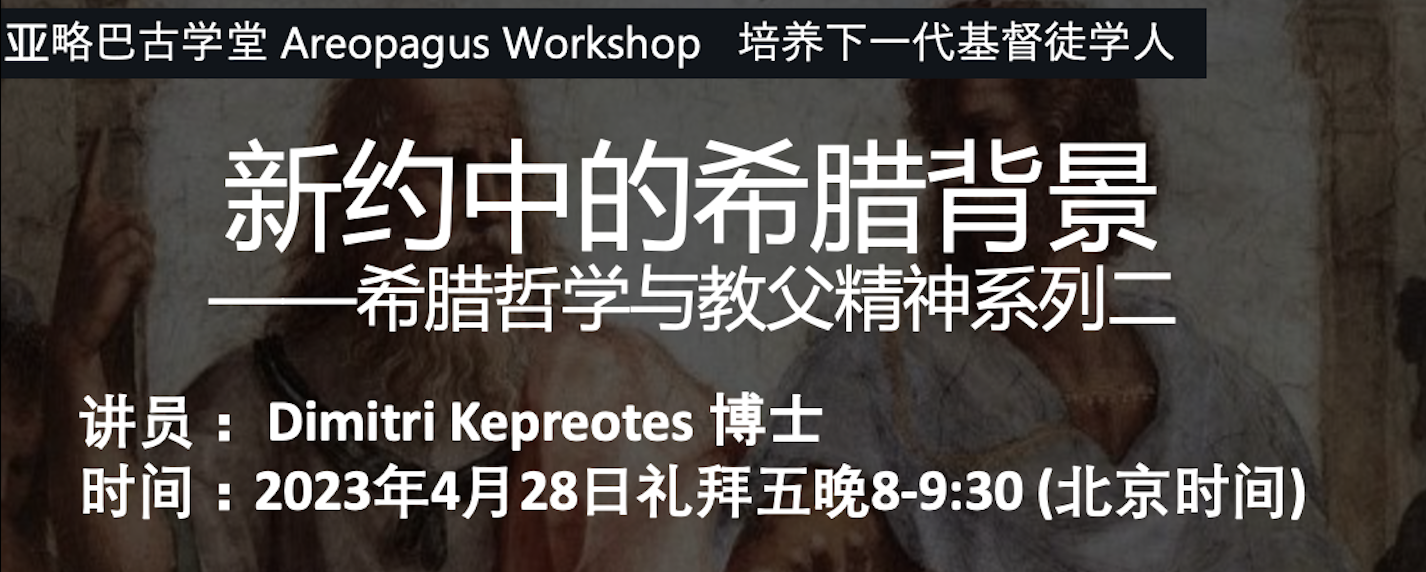Lydia博士:东正教大斋期礼仪中的圣经
按:lydia博士的讲座,东正教大斋期礼仪中的圣经。讲稿初步由阿甲整理好了「等候Lydia老师修订」。注:本文附录了《埃及的圣玛利亚生平》。 版权声明:若要转载或引用此文,请用以下格式:Lydia博士《东正教大斋期礼仪中的圣经》,(伦敦:光从东方来,2025年02月14日网上讲座),附上网页+引用日期。 若要引用本文,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audio音频 讲稿正文 大斋期在教会礼仪年框架中的位置 大斋期崇拜的结构和特色 大斋期崇拜中的圣经 1. 大斋期在教会礼仪年框架中的位置 在正教礼仪中,时间是几个不同的循环交织起来的。首先是每日循环,从抵暮课开始,一天一共七个时刻,然后是晚祷,然后是午夜祷告,然后是向晨课,就是黎明的时候起来祈祷,然后是第一时,第三时,第六时。这就是日循环,那么在这个循环中这个日循环中他的高潮是什么呢?就是弥撒圣礼。那么除了日的循环以外,还有周循环。从周日开始,主日是每周的第一天,一直到周六安息日。周循环的高潮当然是主日圣礼。 此外,还有月循环,年循环。今天咱们关注的是礼仪年,其定义是什么?一般的描述性定义: “…the liturgical year is based on a series of holidays and commemorations that are celebrated throughout a civil year, year after year … ”(Vismans & Hollaardt, LiturgischesWörterbuch, 1965) “礼仪年是一系列贯穿在民事年始终的节日和纪念日,年复一年的进行庆祝。” 以上是从世俗,民事的角度来定义礼仪年。那么神学的角度是什么呢?神学角度的功能性定义: … The liturgical year is a conscious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f the church upon the Mystery of Christ, who truly manifests himself in the rituals of the church, who gives himself to those who come to him and thus sanctify the whole world through them....